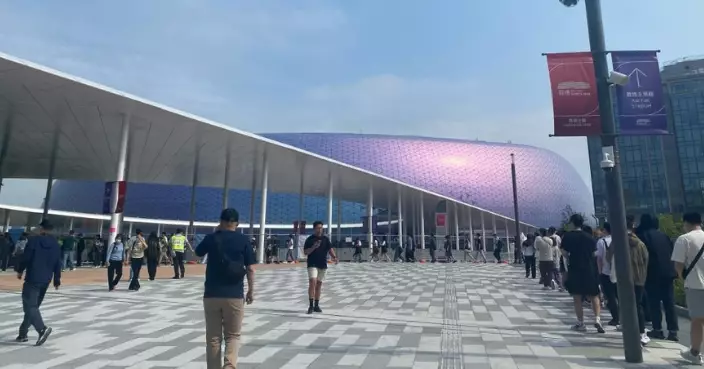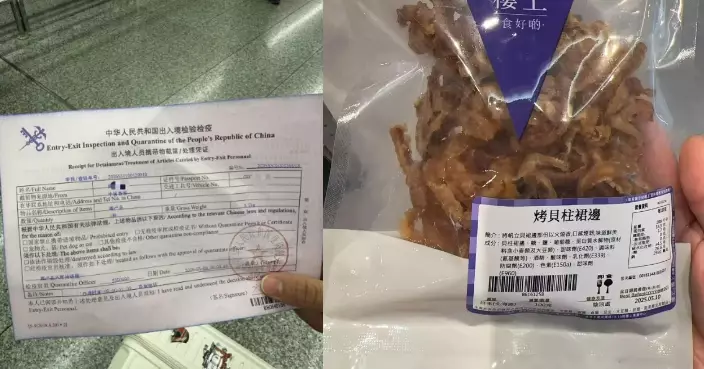愈來愈多時事評論人和政黨開始談論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認同貧窮問題是香港民怨積壓的主因之一。然而,當我們高談闊論「貧窮」的時候,究竟「貧窮」是什麼?政府對「貧窮」的定義是否合理?如果政府的定義並不準確,那麼,能夠對症下藥的定義又應該是什麼?
其實,對於貧窮,世上不存在絕對而統一的看法。例如,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任何人每日收入低於兩元美金(約16元港幣)即屬貧窮;至於近日宣佈成功脫貧的中國內地,則以每年收入8,000元人民幣為標準,低於這個收入水平的人才會被介定為貧窮人口;在美國,貧窮是指一人的年度收入低於12,880美元(約100,464元港幣)。可見,貧窮不同於科學、數學,並沒有全球公認的劃一指標,而是按照各個社會的實際情況,包括經濟發達程度、物價、人均收入等因素而自行調節。
因此,筆者在標題上特別強調「香港」二字,是希望強調和探討屬於香港這個社會獨特而適用的貧窮定義。現時,政府官方介定貧窮的方法,是以自2013年起由扶貧委員會調查及公佈的「貧窮線」為基準,即收入低於住戶入息中位數的50%。按照政府統計處公佈2019年的數據,一人月入中位數為9,000元,故每月收入低於4,500元便是貧窮人口。
不過,扶貧委員會強調,「貧窮線」與「扶貧線」是兩個概念,即使某位市民的入息處於貧窮線以下,政府也不一定提供援助。反之,處於貧窮線以上的人,也有可能符合資格領取部分的社會福利,例如在職家庭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對於處於貧窮線以下人口而言,最常見的援助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等必須符合門檻極高的入息和資產審查方可領取的現金福利;二是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例如公屋。
換言之,在政府眼中,只有能夠符合取得社會福利資格的市民才算是真正的貧窮,而當他們得到有關福利後,則會被視為已經脫離貧窮。因此,在扶貧委員會的最新報告《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以至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說法,都堅稱雖然多達149萬市民處於貧窮線下,但是經「政策協助」後,貧窮人口便「大幅下降」至約60多萬。
然而,以綜援為例,一個健全成人的申請資格,是資產不可超過33,000元。而申領人士能夠領取的每月標準金額,則不過2685元。在香港這個生活成本騰貴的地方,如果有人計算連同現金、存款在內的資產低於33,000元,相信其生活質素已經不單單只是貧窮,而是赤貧。即使綜援受助人享有租金補貼和免費公共醫療等福利,在月入僅僅2685元的情況下勉強維生,難道就不算是貧窮了嗎?
因此,更多基層港人的習慣是自力更生,不依靠政府一分一毫的福利津貼。在最低工資的保障下,只要上班時間和日子不過分地短,基本上其收入肯定在貧窮線之上,甚至超出政府所有社會資助申請條件的上限。但是,這些人朝不保夕、勞勞碌碌的市民,為什麼在政府眼裡就不屬於貧窮甚至不配享有任何社會支援呢?
這個現象衍生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香港政府現行衡量貧窮方法上出現嚴重漏洞,單純以收入判斷市民是否貧窮和是否需要福利補助。可是,雖然收入貧窮是一個相對方便評估貧窮程度的方法,卻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無法判斷該人的生活質素。例如,一個人即使收入頗高,但如果生活必要開支如債務、租金、醫療開支等負擔太大,則該人的生活質素處於貧窮線以下也不足為奇;相反,就算一個人收入較低,處於貧窮線的水平,卻有著豐厚的資產及投資回報,其生活水準也不成問題,此現象在已達退休年齡仍然孜孜不倦投身勞動市場以打發時間的長者中尤為普遍。結果,一大群超出政府「貧窮」界定的有需要市民,便被社會福利保障拒於門外。至於符合社會福利資格的市民,在苛刻的申請要求和微薄的社會津貼下,也輕易地被視為「成功脫貧」。
更加重要的問題是,究竟貧窮的標準以至福利的資格應該如何釐定。以公屋為例,一人公屋單位的要求是申請人的月入不得超過12,800元,至於三人單位,申請人之月入則不能多於24,140元;但是,根據學生資助處有關中、小學生書簿、交通及上網津貼,三人家庭月入必須低於13,800元方可得到全額資助,月入高於16,000則連申領半額資助的資格都失卻。在此,筆者必須質疑,既然住屋開支和子女教育開支都是家庭的重大負擔,兩者同樣有著舒緩貧窮問題的重要作用,那麼,為什麼取得相關福利的準則就差距甚大?
從以上幾項社會主流福利項目可以看出政府在有關問題上的三個重要思路,第一,雖然在政府眼裡,需要領取相關福利的市民就是貧窮人口,但是貧窮的定義存在很大的彈性空間,不同項目的申請條件並不一樣。至於能夠定義每個項目申請資格的單位,就完全掌握於政府手中,項目的受惠人數和援助程度取決於其扶貧思維和策略。第二,現時政府對於扶貧的思維和策略,是為合資格人士提供香港社會裡最低程度的生活條件,使申領人有機會獲得住所、食物、水電、教育等現代社會的最基本生活質素,但不會額外考慮提供基本生活以外更多的支援,否則申領人就必須跳出社會福利制度。第三,雖然各項福利的資格是浮動的,不過由於政府的扶貧策略只是提供最簡單和最低層次的生活支援,所以還是可以看出政府的目標群眾,大約是月入13,000元左右或以下的人士,而處於這個收入水平以下的人,則有著不同程度的支援,如相對接近上限的市民,就只有申請公屋資源;處於最底層的,則可獲得綜援等現金支援。至於在政府眼中不符資格申請福利的市民,就是沒有明顯經濟和生活困難,無須政府幫助,能夠「自力更生」的人了!
但是,既然政府在貧窮問題上有著至高無上的決定權力,政府的扶貧思維卻只停留在最低層次的生活援助,從而只能舒緩一部分基層市民的困難,明顯已經脫離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和隨之出現的階級結構的步伐。
香港過去幾十年經歷深刻而劇烈的產業變化,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輕工業和製造業為主的經濟體系,在經過產業轉型及擴大高等教育等因素下,逐漸轉變為以金融、服務、文職為主的發展模式。以前絕大部分的勞動人口是工人,即是屬於基層。相反,現今主要的勞動人口則是文職白領,而按照他們的收入水平,除非是專業人士、管理階層、企業精英、否則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質素遠不如中產優越和舒服,但是又稱不上是基層,筆者故且稱他們是「夾心」。
如果我們按照政府粗疏的階級劃分方法,即單純以收入水平作為指標,則可以發現夾心階層其實才是社會的多數。根據2020年第一季的數字,收入介乎10000元至30000元的勞工,佔整體勞動人口高達54%,約190萬人。至於收入在10000或以下的,約佔10%,意味著月入30000或以上的市民,大約有36%。當然,部分月入介乎1萬至3月的群組當中,可能部分都是正在領取或合符資格領取社會福利的基層,但即使扣除這類人士,夾心也無可否認仍然佔有相當突出的比例。
可是,政府對收入貧窮的盲目崇拜,僅僅願意向收入偏低的人士提供社會保障,令同樣面對嚴峻生活壓力的夾心,難以分得政府福利的一分一毫。於是,夾心的生活質素和前景,便如日本社會學者大前研一的說法「M型社會」一樣,因為中產階級的萎縮,而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擴大,面臨逐步下流的困境。
因此,香港思考和扶助貧窮的方法,必須摒棄昔日只是著重收入貧窮和視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就是脫離貧窮的守舊思維,重新建立和認識香港這個發達先進社會中應有的貧窮定義。明顯地,這種貧窮不再是純粹的收入貧窮,亦未必需要及不能單靠現金補助以解決,重點是在於看見夾心的內在貧窮。
內在貧窮與收入貧窮不同的地方,是內在貧窮不是硬性的指標和數據,不能按照客觀標準量度,而是更加接近於一種生活和心理的狀態。具體而言,內在貧窮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是「機會貧窮」。英國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著作《工作、消費與新貧》和《全球化》分別指出,在全球化仍未成熟的年代,不少企業或工廠都採取類似日本的營運模式,有著嚴謹分明的人員架構。每個職級都會因應上級的升遷或退休而取而代之,變相只要員工在機構內服務一定時間,就必定得到相應的機會。加上當時普遍採取「終生聘用制」,除非特殊原因,否則終其一生都可以在同一公司中任職。因此,當時的僱員因為大多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相對容易作出人生規劃,如置業、成家、生育等等。
不過,全球化的來臨,促使這套曾經大行其道的企業制度和文化在激烈的競爭下蕩然無存。企業為了增加優勢,想盡辦法節約成本,要麼大幅削減中層管理人員職位,要麼轉移生產基地,搬遷企業至其他營運成本較低的地方。於是,由於有助提升階層地位的職位在市場中大量流失,社會流動的機會便大幅減少。
雖然筆者未能收集過去數十年間,社會各個階職的職位數字的變動,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憑著由政府統計處分別在1996年和2011年進行的《經理級與專業僱員薪金及僱員福利統計報告》找出呼應機會貧窮的證據。向來是香港經濟支柱的金融業,在1996年該行業有多達25個工種的薪酬被列入調查和統計之中,到2011年,相關工種已經減少至18個,意味即使發展蓬勃的金融業,同樣出現中層職位流失的問題。情況更加嚴重的有另一支柱產業 – 貿易,1996年貿易界別有13個工種列入統計對象,到2011年則減少至9個。其中,部分工種如出入口經理、財務或會計經理等職位的工資增長遠遠落後同期各行業約30%工資增長的幅度,有崗位(商品部經理)在15年間工資甚至完全沒有變化。
機會貧窮造成的最大問題,就是除了少數精英、具背景或運氣甚佳的人,社會長期出現一大群人處於相約的社會階級,既難以力爭上游步向中產以享受相對優質的生活,也未能進入社會安全網享受福利保障。在社會財富兩極化愈趨嚴重的情況下,夾心充滿對階級下流的恐懼,對生活前景感到悲觀和憂慮。
第二種貧窮是「安全貧窮」。誠如上述,現時香港的社會安全網,只是針對在這個先進、發達的社會中屬於「赤貧」,即社會最底層的一群,並根據不同程度的赤貧發放不同類型的社會福利。以最極端的赤貧為例,便可以領取綜援的現金及基本生活保障;次一等的赤貧,則可以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少額現金補助;再次一等的則可能是非現金補助,而是個別必要開支的津貼或支援,例如學童車船、書簿津貼或公屋等等。
表面上,香港社會安全網能夠幫助赤貧人士,一定程度上舒緩他們的生活困難。可是,只要細心一想便會發現這個所謂的安全網的目標和對象非常保守和迂腐。由港英年代至今,香港社會安全網存在的目的,以至其實際提供的支援,都是充滿著「新自由主義」的色彩。政府的行為如同右翼自由主義者Robert Nozick的倡議一樣,維持在「小政府」(minimal state)的狀態,避免承擔過多照顧弱勢市民的責任。即使政府提供福利,主要作用也是維持一個公民在社會中最基本、最簡單的生活需要,減低因貧窮所衍生的社會成本(例如動亂、城市儀容、治安問題),而不是出於守護或建構人的尊嚴、或是承認社會福利是公民權利的角度出發。
由於政府本身就不傾向提供完善的福利制度(甚至是鼓勵市民離開安全網),所以安全網的對象,只是覆蓋社會上的赤貧人口,一旦在收入或資產方面稍稍超出赤貧的定義,則幾近與社會福利絕緣。不過,必須指出,雖然夾心的確在收入上比赤貧、基層為多,但其生活質素則不一定較好,因為前者幾乎不能享有各種社會福利,而且需要自行承擔住屋、醫療、教育等各項家庭必要開支。在扣除這些生活成本之後,夾心能夠消費和儲蓄的金錢可能比一個基層更少,尤其是那些收入水平只是僅僅高於政府福利標準的人。對於夾心而言,他們唯一可以享受的社會福利,便是十多年前一度消失、現在重新推動、資源卻杯水車薪、僅得2%成功率的居者置其屋計劃(居屋)。
美國社會學家Richard Sennett在經典著作《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提到,人的價值、尊嚴和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工作,工作帶來的產出、回報和性質成為人自我肯定的一個準則。可是,在工業化、全球化和智能化的年代,人與工作的關係變得疏離,工作不再成為人類穩定而可靠的生活質素和自我價值的來源,因而逐漸出現不安的情緒。可惜,政府的政策思維未能追上當今社會發展的步伐下,對於這群因為大環境迅速變化而產生內心不安的夾心拒於社會保障的大門之外。即使夾心選擇領取社會福利,也只會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一,放棄現有的工作和生活,接受政府僅供維持低度需求的補助,正式流向赤貧;二,奢望和等待政府提供小量容許夾心人士也可以申領的社會資源,期間繼續苦苦掙扎。可見,夾心不論在社會或工作中基本上都難以得到維持其生活質素的有力依靠,使其不安感覺愈趨強烈,甚至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
第三是「尊嚴貧窮」。由於單憑工作已經難以促使夾心向上流動,政府亦不願為夾心提供社會保障,因此絕大多數的夾心都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繼續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嘗試在中產與基層之間的生活游走。可是,正正因為夾心沒有優厚的財富,工作又充滿不穩定性,更不願生活每況愈下而變成基層,於是對於無理的工作要求只能低聲下氣,逆來順受,工時問題正是一個最佳例子。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資料顯示,全球每年人均最高工時的地方,是美洲國家墨西哥,達到2157小時,即每星期工時約41.5。然而,根據立法會的研究顯示,香港每星期的平均工時為42,即每年工時為2184小時,工時問題較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如哥斯達黎加、智利等更加嚴重,是世界上除新加坡以外工時最長的地方。
工時過長,甚至工餘時間都不能避免工作指令的騷擾,進而影響個人健康、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除了是因為香港直至目前仍然沒有立法規管標準工時、甚至整套勞工保障制度依然漏洞處處之外,亦因為夾心人士缺乏討價還價的籌碼。為了維持現有的生活和寄望未來待遇有所提升的可能,根本無力拒絕資本家對勞工的任意剝削和踐踏。
根據2019年職業安全健康局委託嶺南大學進行「工作壓力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研究報告,港人因為工作壓力而缺勤的日數高達8.3日,缺勤及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比新加坡、加拿大等地更加嚴重。這項研究不單反映港人工作壓力巨大,亦說明夾心除了缺勤等方法外,根本沒有選擇面對或逃避的方法,勞動尊嚴極為低微。加上工作壓力和待遇帶來的健康、家庭、私人生活等問題,令夾心感到彷徨無助。
憂慮、不安、無助、絕望,是普遍夾心的心理寫照。當大量夾心對當前生活和未來前景感到負面,而他們因政府政策沒有伸手支援而感到被排斥和遺棄,這種內心貧窮便會逐步轉化成不滿和憤怒,而排解的出口就是政治宣洩,進而引發影響深遠的社會動盪,最終反而造成貧窮問題加劇。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回歸以來,人數不斷擴大和處境持續惡化的夾心階層在政治上的參與愈來愈多且愈趨激進。
既然貧窮問題不僅局限於赤貧的基層,而是收入水平稍高一層的夾心亦深陷其中,那麼,究竟怎樣才是解決貧窮的最佳辦法?更準確地說,在扶貧問題上,政府應該有著怎樣的思維呢?
社會學及歷史學家Jared Diamond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先有落後國家還是先有文明國家。一般人的想法,當然是先有落後國家,因為世界的發展是向前推進,所以每個國家都自然是由落後過渡至文明。但是Jared Diamond的想法恰恰相反,正是首先出現文明國家,他們才會意識到與其他國家的分別,繼而標籤自己是文明、對方是落後。
扶貧的思維亦應如是。現時政府在社會福利的政策思維,與世界各地的政府相差無幾,就是
只從如何免於赤貧的角度出發思考貧窮問題。於是,政府提供福利的對象,只是一群假如沒有政府援助,將無法在香港這個繁華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社會底層市民。至於政府的福利,也是限於住房、醫療、日用品開支等令他們僅僅足夠生存下去的金額。
如果我們不是思考「什麼是貧窮」和「如何令人離開貧窮」,而是思考「什麼是富足」或是「什麼才是中產生活」,即是將思考的角度,由保障有需要的市民在這個百物騰貴的社會之中如何勉強生存,改變成保障有需要的市民在這個百物騰貴的社會之中盡可能地輕鬆生活,那麼不止是基層,連夾心都一樣可以受惠。
當然,一定會有人質疑,世上根本不可能對「中產生活」有一致的看法,因為每個人的想像和期望都不可能一致。然而,筆者必須反問,難道貧窮的標準就不是人言人殊嗎?政府對貧窮的定義難道就是社會共識,無人異議嗎?其實,中產或富足生活的定義並不復雜,就是達至「餘裕」,在扣除必要生活開支後仍然有足夠的資源進行儲蓄、消費、甚或投資,使其生活壓力、不安、憂慮等負面感覺減至最低。
正如上文提到,收入不算太低的夾心,需要的未必是直接的現金資助(從政府財政負擔角度,也是極不現實),他們真正的需要,是在這個缺乏安全感的社會之中,由負責分配公共資源的政府,在政策上提供「餘裕生活」的保障。這些保障可以包括,放寬公屋申請入息和資產條件,讓夾心無須承受承擔私人市場的高昂租金;增建居屋及放寬申請資格,使有需要成家立業的人有相對合理的上樓選擇;提供首置貸款或調低居屋價錢,減輕業主供款壓力;制訂標準工時和「離線權」,改善勞工工時過長及壓力過大的問題,真正享受工餘時間平衡生活;降低各項津貼如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學生車船書簿津貼等,使夾心同樣受惠;設立失業援助,為夾心勞動者享受更多勞動尊嚴;設立創業及周轉貸款,使有商業觸覺的夾心跳出勞動市場,成為小本經營者享受更多自由等等。以上的政策倡議不一定是直接的現金援助,但是同時也不會令政府開支變成無底深潭,為夾心提供適度的安全網,在大風大浪的環境之中有一個可以依靠的避風港。
香港社會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承襲上世紀70年代的英殖年代。但是,過去數十年間世界發展和社會結構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政府依然抱殘守缺,只是懂得為最有需要的市民提供人道援助的話,社會怨氣和對立的問題只會日益加深,終致不可收拾的境地。筆者強調,貧窮問題已經不再只是基層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滿足勉強生存的需要,而是要擴大受助層面和幅度。當政府真正改變扶貧思維,正視多數市民的困難和需要,才有望真正實現安居樂業。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