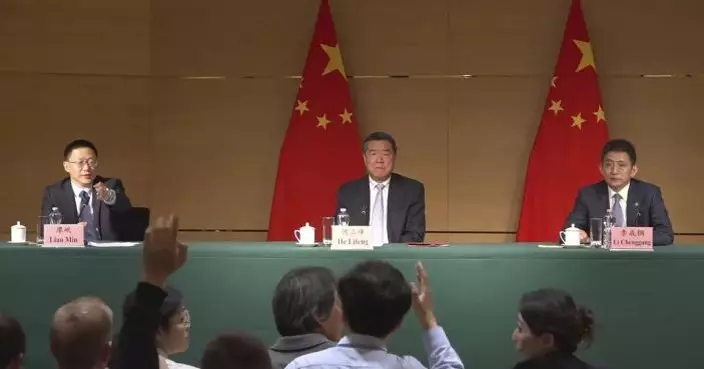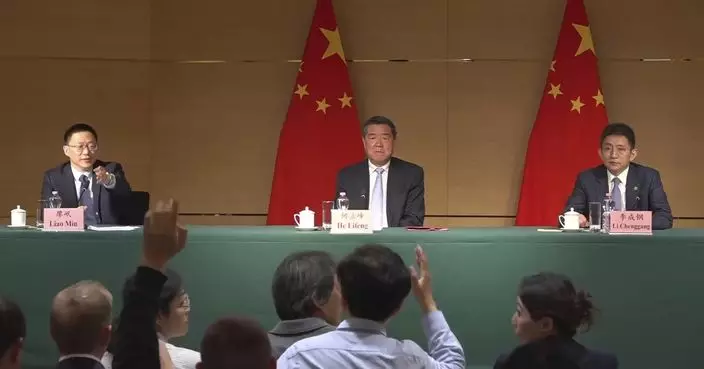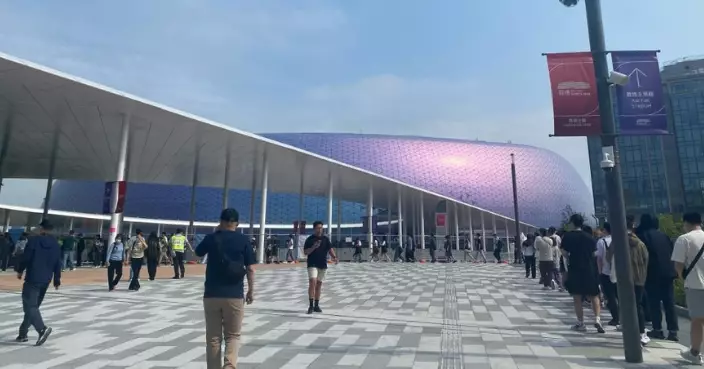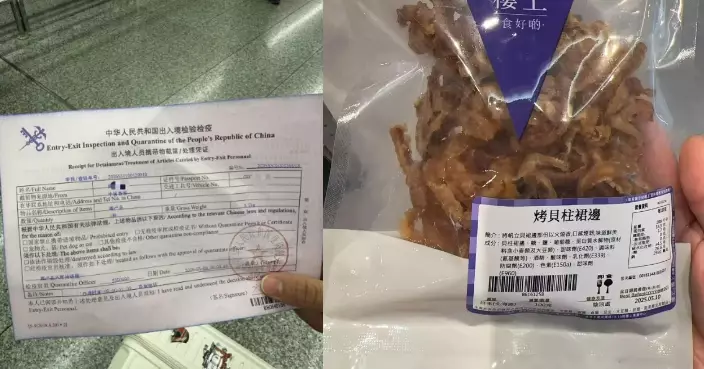盜印,是指未經作者或版權所有者允許的情況下,擅自覆制或印刷他人的著作。這種行為在中國早已有之,比如清朝袁枚的作品曾多次被盜印,但這不代表中國古代完全沒有版權保護的意識。相反,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知識私有觀念就悄然萌芽。
戰國以前,學在官府,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政教合一。除了由國家職官,如師氏、保氏、大司樂、等掌握學術的人來擔任各級學校的教師,學校也從施教的場所變成進行政治活動的場所。因為官府壟斷學校教育和學術文化,所以天下未有私人著述的文字,也談不上什麼盜印。

西周教育的顯著特點有三:禮不下庶人、官師不分、政教合一,而這也是西周教育制度的高度概括。簡單來說,「學在官府」就是學術和教育為官方所把持,國家有文字記錄的法規、典籍文獻以及祭祀典禮的禮器全部掌握在官府。(網上圖片)
到了戰國時期,官守師傳之道廢,時人也開始嘗試把舊聞寫在竹帛上,這也是私人著書立說風尚的開始。既然有了民間書籍的出現,自然少不了署名權,不然都不知這書是何人所著。在思想交鋒與激盪的時代,諸子百家學說紛呈,他們的書多以「某某子」為名,例如《墨子》便是墨家思想的總集。這種命名方式簡單直接,讓人一眼就知道書自何派,而這也是我國著作署名權的起源。
不過這種著作署名權其實不大公平。不論是《墨子》、《老子》、《莊子》,還是《孟子》、《荀子》、《韓非子》,都不是學派領袖能夠獨立完成創作的,不少書籍都是在門人弟子的協助下編寫而成。因此,署名權在成為門派代表人物的專利變相剝奪了弟子們的署名權。這也沒辦法,終歸是版權意識的萌芽階段。除了諸子著作之外,先秦其它著作也大多沒有署名,這為漢代劉向等編寫《七略》帶來不少麻煩,《儒家言》、《道家言》、《雜陰陽》、《法家言》、《雜家言》等著作至今仍不知著者為誰。到了漢代,卷端署名之例開始大量出現。晉代以後,著作卷端無不署名,這說明版權、署名權等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從古籍記載來看,抄襲、剽竊、盜版等令人不齒的行為,但其實有不少都是文化人牽頭做的。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創作史上的「抄剽第一人」應是《漢書》的作者班固。雖然不能否認班固在史學上的貢獻,但他著史時的不端行為與《三國志》的作者陳壽一樣,一直飽受後世指責。據學者研究,從漢高祖到漢武帝這段歷史,主要剽竊了司馬遷的《史記》。除《董仲舒傳》外,《漢書》的內容跟《史記》完全沒有實質的變化;從漢昭帝到漢平帝這段歷史,則大量引用同時代賈逵和劉歆等人的作品。(網上圖片)
到底版權什麼時候才真正被人重視呢?那就得等到唐代雕版印刷問世之時。中國古代社會的早期沒有版權的觀念,是因為不存在產生經濟權利的基礎。換句話說,在傳播技術還沒有發展起來前,刻印出版商及作者並不會因傳播或創作而得益;沒有傳播的途徑,作品的社會價值也難以實現,所以唯有圖書制作方式發生劃時代變革,著作的發表權、修改權、使用權、獲得報酬權才開始引起人們關注。
然而,雕版印刷的出現也會引起我們文章開首提到的問題——盜印。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東川節度使馮宿上奏朝廷,請求頒發赦令,禁斷民間私印歷法。根據馮宿上的說法,每年司天台都沒頒發新歷,盜版的日歷已經遍佈街頭,實在有違敬授之道。這份奏疏得到了唐文宗的批準,自此歷法版權收歸中央。這次盜版打擊行動除了強調了歷書的神聖性,但其根本目的不外乎是要打擊和杜絕盜印。詔令頒佈後,民間自印曆自是不敢這麼猖狂。就算想翻刻曆書,也必須征得欽天監同意。由於翻刻的曆書都是民間盜印,所以總是錯漏百出,一日半日的推算失誤都是小事,所以禁止私印其實也是保護了原編者的聲譽和作品的完整性。
當然,不是所有書都像曆書般可以受到皇室的保護,其它私人著作的盜作問題依然嚴峻。唯有到了宋代,人們私有財產觀念進一步地深化,才有了相關民事法律的發展。北宋慶歷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印刷術的出現與發展讓圖書印刷不再局限於佛經和日歷,使盜版圖書的門類也越來越多。加上,一些書商為利益所趨,竟胡亂刻印,這導致圖書質量嚴重下滑。因此,治平之前,皇室決定發布刻書禁令,禁止百姓隨便刻書。如有需要,則須向國子監申報登記。在國子監嚴格審查後,才準許付梓。治平之後,禁令雖稍有放松,但仍依然存在,違例者可要「徒二年」!

雕版印刷是最早在中國出現的印刷形式。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敦煌莫高窟發現,印製於唐朝公元868年的《金剛經》(現存於大英圖書館)。(網上圖片)
雖然有朝廷已經採用版權保護手段,但仍未能杜絕抄剽和盜版行為。把他人書稿改頭換面再出版或直接改個名字翻刻印刷的現象仍舊普遍,譬如司馬光的《歷年圖》就被趙姓小人改為《帝統》,然後用於刻印賣錢,甚至明代俞羨章為了保護自己作品,想出懸賞捉拿的主意。俞羨章編有一部唐代類書匯編《唐類函》,為了不被侵權,在該書即將竣工之時,俞羨章向官府投遞了一張訴狀。訴狀稱新印成的《唐類函》被強盜劫去,懇請官府捉拿盜書賊。官府遍出告示後,懸賞緝拿。這樣一來,就沒有人再敢盜印了,真的是用心良苦!
正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明代刻書業發達,在如此大的書稿需求量下,盜印、抄襲問題越來越猖獗。《四庫全書總目》就這樣批評明朝的出版書:「是書雜采小說家言,湊集成編,而不著所出。」難怪到後來,新書都不像宋代般印上作者的「牌記」。
面對抄剽之風,時人反應迴異。有的人恨不得搭上盜版快車,恨恨撈一筆;也有人像蘇東坡一樣,認為讀盜版書「使人不平」。無論如何,盜版猖狂得連官方都無能為力,作者們又能怎麼辦?唯有調整自個心態,順其自然。袁枚就是個好例子。面對「不佳者」,袁枚就一笑置之。遇上「詩序俱佳」,則會買來欣賞,氣度非凡!

宋代出書時,封面後或封底上已開始印上「牌記」,版記里印有作者、出版者名號、版權聲明等。如當時出版的《東都事略》一書內頁上,長方形牌記中便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宋王季平先生著」、「振露堂藏版」等字樣。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國版權保護例證,也是「版權所有,不許翻印」最原始的出處。(網上圖片)
其實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出現過「版權」一詞,法律語境下的版權(著作權)也是近代以後出現的新詞,甚至是日本人從英語copyright翻譯過來的外來詞。直至1903年,「版權」一詞才首次在中國出現前。因此,國內版權保護處於零星少變的狀態也是有跡可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