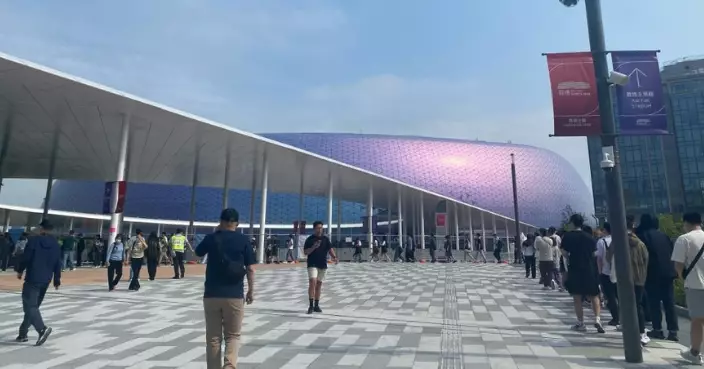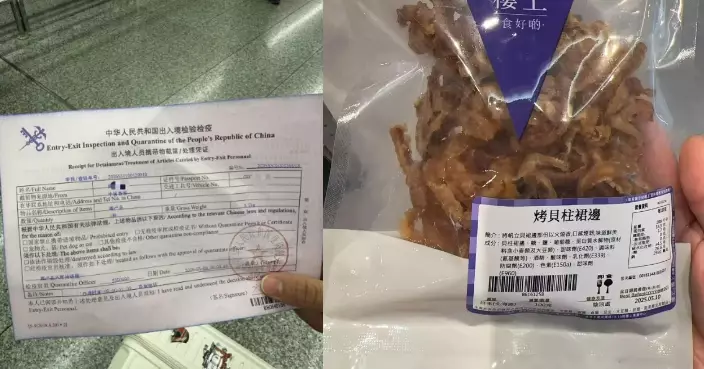「抑鬱症是可以說出來的。」科大商業教育學者霍士德(Paul Whitfield Forster),二十年來從不缺課、屢獲教學獎,卻無人知道這名謙謙君子背後,已與抑鬱症交戰半生。霍士德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坦言,曾因懼怕醫療紀錄影響仕途不敢求醫,一度以酗酒、猛吃安眠藥來麻醉自己。直至三年前兒子突然患上思覺失調症,作為兒子唯一的依靠,他深知絕不能被抑鬱情緒壓垮,努力靠服藥及冥想重新振作。一路走來,他看待抑鬱症的心態已然轉變,更期望以自身經歷勸勉同路人,「你有抑鬱症不代表你是失敗者。」
眼前這名科大工商管理學院管理學系副教授,頭髮雖已斑白,看起來卻較實際年齡年輕,「我是一九五九年出生,來自夏威夷的媽媽是百分百華裔,爸爸則是紐西蘭人。」霍士德展示一張童年照反問:「我看起來像中國人嗎?」相信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會認為,他是不折不扣的混血兒。
「在西方人眼中,只要與他們白人長得不一樣,便是異類」霍士德說。八、九歲的他隨父母移民美國及加拿大,受盡種族歧視及欺凌,對他的成長造成嚴重創傷,令他變得自卑,「我無法忘記這一切,他們會令你覺得自己是錯的,你卻不能改變與生俱來的膚色。」
積壓負面情緒於「爆煲」
自此他成為「獨家村」,只與同屬少數族裔的猶太、印度裔同學交朋友,內心的焦慮及孤單感卻不減,對外時總是裝上盾牌,久而久之也忘記處理積存心底的負面情緒。直至父親患癌病逝、剛出生的兒子夭折,經歷失去至親之痛,他的情緒終於「爆煲」,焦慮更演變成憤怒。
有次霍士德駕車到油站時有職員入錯油,他突然情緒失控,跳落車呼喝職員,更想對其動粗,「當時我完全變了另一個人般,所以去了尋求協助,原來我患上抑鬱。」服藥後他的病徵得到紓緩,但病情一直反反覆覆,一旦進入抑鬱期,他便會情緒低落、失去動力。完成博士學位後,霍士德於二○○○年加入科大,並舉家移居香港,怎料剛開始適應生活,便經歷中年失婚,搖身一變成為單親爸爸,加上工作低潮、積蓄盡失,他再度陷入抑鬱。但今次他沒有主動求醫,反而開始酗酒,試過每日喝掉半支伏特加,猛吃安眠藥、吸煙來麻醉自己。
他形容自己所患的「功能性抑鬱」既是祝福又是詛咒,雖然不影響他日常的教學工作,不會因病缺課,但每晚回家卸下面具,他始終要面對一大堆生活壓力,不斷來回地獄及人間。幸得學生介紹他學習冥想,鍛煉自我思想及學習「let go(放開)」,成功將他從痛苦中拉回來,更令他醒覺要摒棄惡習,重新服食抗抑鬱藥,重投正常生活。
為病兒重新振作
可惜好景不常,一向品學兼優、充滿創意及運動細胞的兒子其後確診患上思覺失調症。獨自照顧患上精神病的兒子,霍士德感到很大壓力,而抑鬱症這老朋友,也再次來探訪他,令他活在哀悼之中足足一年。作為兒子世界中的唯一,他深知不能被抑鬱情緒壓垮,於是努力靠服藥及冥想,令自己重新振作。隨着年紀愈來愈大,每當他想到自己可能較兒子走先一步,便難掩作為父親的擔憂,「我只想趁我還在,繼續充當兒子的聆聽者,陪伴他散步,了解他眼前的『現實』。」
與抑鬱症共存近三十年,他坦言從沒想過這麼坦然面對,與這麼多人分享,「這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年輕時的我也曾擔心確診後,當醫療紀錄寫我患有抑鬱症,會為我的工作帶來危機,影響別人對我的看法。但原來,抑鬱症是可以說出來的。」
霍士德寄語同路人或懷疑患有抑鬱的人,當負面情緒不能自控、久久不消散,便要尋找信任的人傾訴,「要記住,你有抑鬱症不代表你是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