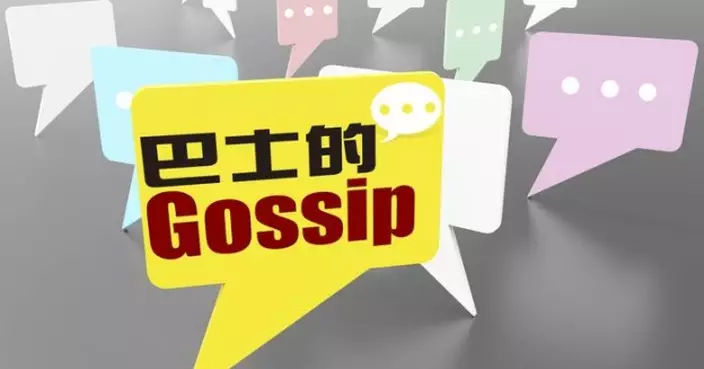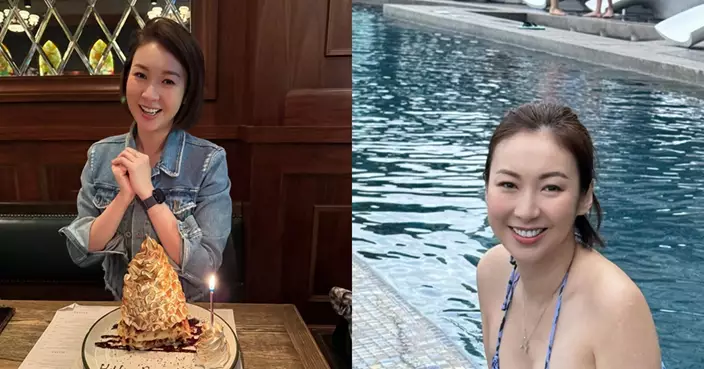選委會選舉在沒有吵鬧聲中結束。泛民自己拒絕參與選舉,之後又批評這次選舉結果是「清一色」。但清一色又有什麼問題呢?過去香港實行五顏六色的民主制,回歸24年,民主越搞越多,到底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了問題?不妨看看香港政治、民生、經濟的有什麼問題。
第一、 政治上最大的問題是動亂與失效。在我讀大學的年代,學者話「匯豐、怡和和賽馬會管治著香港」,社會的權力被富裕階層壟斷了。政制改革的原本假設是香港實踐民主制後,會增加了普羅市民的參與,打破財團的壟斷,令社會變更加公平,並可以消除草根階層激進反對的根苗,令政府可以更加高效運轉。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極殘酷。回歸24年政制不斷開放,但帶來的卻是動亂和失效。爭取民主由一種為追求良政善治的手段,變成民主本身就是目的,民主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政府每次提出檢討政制,希望進一步發展民主,都會觸發更大的動亂。在議會上未佔多數的反對派,為了擴大其權力,就用拉布等各種方法癱瘓政府,令管治失效。民主沒有解決問題,更製造大量問題。爭取民主的過程,變成問題本身。
過去一年,反對派不參加延任的立法會,議會忽然變得高效無比,在一年之間,通過了24條法律草案、通過3100億元的撥款,將因拉布而積壓多年的撥款項目快速通過,令到政府施政的效率一下子大幅提高。議會清一色,不再有混亂,提高了效率。
第二、 民生最大問題是高樓價。香港搞了24年民主,樓價是升了還是跌了呢?猶記得回歸之前,香港市區樓價幾年內由每方呎4000多元,到1997年炒上1萬元。港英政府為了平抑樓價,在1997年一年推出3萬個居屋單位,如果港英政府當年沒有狂推居屋,恐怕97年樓價可能已經升到2、3萬元。1997年,民主黨的李永達上街遊行,說香港人已變成「無殼蝸牛」。
24年過去,香港民主了,但樓價失控了。議員們通過一條又條減少供應的法例,市區樓價由97年的1萬元高峰,升到3萬元,去到一個正常人負擔不起的水平。我上網搜索究竟有什麼團體曾反對過高樓價,結果只找到「愛國工會」曾發聲抗議,其他的政黨、特別是反對派政黨,對高樓價問題視若無睹。香港政黨的「離地」,已經去到一個驚人地步,是無能還是有利益呢? 所以,將民主看成萬金油,以為越多民主,就能夠解香港所有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笑話。我的經驗是越多民主樓價越貴。
大家見到星期一新一屆選委會選出前後,有傳聞阿爺約見地產商,說要解決香港高樓價的問題,主要地產股暴跌超過一成。香港過去哪一次民主選舉,選完之後樓價會下跌的呢?香港的民主鬥士,面對捱貴樓的市民,應該無地自容。
第三、經濟缺乏發展前景。2020年底,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46330美元,香港經濟已進入高原狀態,要尋找新增長點已經非常困難。幸運的是,香港處於內地高增長的巨大引擎旁邊,香港只要加強與內地融合,水漲船高,理論上「扯著衫尾」也可以找到新的出路。但反對派骨子裡就是反共,推動港獨思想,全面排拒內地的一切,在經濟上,鼓動年青人抗拒與內地融合。香港本應要搶生意,卻變成揀生意,揀飲擇食,自斷出路。
香港回歸後搞了這麼多民主,不但沒有解決到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什麼問題,反而製造出重大問題。所以,說解決香港的問題的方法是要有更多民主,其實是只是一個循環論證。
當爭取民主由手段變成唯一而終極的目標之後,所有的討論已經變得非理性。要解決香港問題,只能跳出「民主萬金油論」的邏輯了。
盧永雄
面對一個開口就來的美國總統,我們也得開口就來。
在中美即將進行關稅對話前夕,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保守派電台主持人修伊特訪問時說,「我認爲談論黎智英是非常好的主意,我們會將之納入談判中之一環。」一個關稅會談和黎智英有什麼關係呢?如果美國這樣喜歡談政治問題,中國也可以談談政治問題,更值得討論的是美國錯誤驅逐的薩爾瓦多男子加西亞。
加西亞現在於薩爾瓦多叢林中的「反恐怖主義監禁中心」囚禁,這是全美洲最大的超級監獄,所有囚犯全天候監控,每人都要剃光頭,只能穿着白色內褲,一天只有半小時可以離開牢房活動,睡在沒有床墊的不銹鋼板上,禁止使用任何餐具,只能用手進食,一日只有一桶水供飲用洗漱,生活條件極為惡劣,更被斷絕與外界一切聯繫。外界以「世上最恐怖的監獄」、「無路可逃」和「有去無回」,來形容這座超級監獄,加西亞就是囚禁在其中。
加西亞是薩爾瓦多人,1995年在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出生,母親經營食品生意,遭當地幫派Barrio 18勒索,並威脅逼他的兒子加入幫會。加西亞爲逃避暴力威脅,尋找更好生活,在2011年,他年僅16歲時,就逃離家鄉,非法進入美國。5年後即2016年,與美國公民蘇拉結婚,其後育有3子女。
2019年他在馬里蘭州喬治斯王子縣一間家得寶店外,尋找臨時工作時,被美國警察拘捕。美國警方後來將他移交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啟動遣返程序。當局聲稱他是MS-13幫派成員,理由是他穿著芝加哥公牛隊棒球帽和連帽衫,亦有一個所謂秘密線人聲稱他參與紐約當地的MS-13幫派,但他否認和任何幫派有聯系。
加西亞後來申請美國庇護,但在美國庇護申請必須在抵美一年內提出,他的申請已經過期,因此最終被拒,但法官仍授予他「禁止遣返身份」,認爲不能夠將他遣返薩爾瓦多,因爲「他很可能在被遣返後遭到幫派暴力傷害」,其後將他釋放。
特朗普上台後,辣手對待移民,引用一條古老法例《外國敵人法》,在3月驅逐200多個委內瑞拉人和23個薩爾瓦多人。特朗普急於驅逐這些非法移民,是想盡快向支持者顯示他的反移民政績。當時很多拉丁美洲國家都拒絕接收被遣返的移民,但特朗普就和薩爾瓦多的出位總統布克爾傾好數,這個被外界指控獨裁的總統,大力打擊黑幫,並在薩爾瓦多設立那座恐怖監獄。

被錯誤遣送往薩爾瓦多超級監獄的加西亞。
布克爾爲了拉攏和特朗普的關係,就承諾收取美國支付的費用,接收薩爾瓦多和非薩爾瓦多籍的美國非法移民,將他們全部囚禁入那座超級監獄之內。加西亞今年3月12日在回家途中,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人員截停,告知他「移民身份已經更動」,隨即將他拘捕。3日後,加西亞搭上美國政府的飛機,移民局人員聲稱他和犯罪組織有關,將他們全部遣送到薩爾瓦多的超級監獄,自此加西亞無法再與家人取得聯絡。
不過,特朗普政府事後承認,將擁有「禁止遣返身份」的加西亞送走,是一項「行政錯誤」,但是這項錯誤無法透過美國的司法程序糾正,理由是美國法院對身處薩爾瓦多的加西亞無司法管轄權。4月4日,聯邦法官希尼斯頒令,要求當局必須不遲於4月7日將加西亞送回美國,但是特朗普政府很賴皮地無視法庭的命令。
4月14日,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訪問美國,和特朗普在白宮會面,當時包括CNN在內的美國記者,紛紛追問加西亞的案件,問加西亞如何能夠被送回美國。特朗普和布克爾嬉皮笑臉地互相推諉,特朗普先諷刺一下提問的CNN無觀眾,就交由其他官員回答,在場的美國官員又說他們對身處薩爾瓦多的加西亞無管轄權。同在現場的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說,他不會將加西亞送回美國,認爲這是一個荒謬的問題。在白宮這個嬉笑式的對答中,加西亞的自由和人權,完全被特朗普政府無視。
特朗普政府急於展示遣返非法移民的功績,那個好像芭比公仔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曾經在3月26日訪問薩爾瓦多的超級監獄。她站在牢房外,以一大班剃光頭、赤裸上身只穿短褲的薩爾瓦多囚犯作爲背景擺拍,並聲稱其他人進入美國,都可能面對牢房那班犯人同樣的後果,直指「這處設施將會是美國工具箱裏會使用的工具之一」。這些囚犯連面孔也沒有被打格,所謂私隱和個人權利,不知誰去管了。

美國那個像芭比公仔的國土安全部長諾姆,以薩爾瓦多囚犯作爲背景擺拍,無視囚犯的人權。
或許加西亞的故事,可以用特朗普的評論作結。特朗普在4月21日接受NBC訪問的時候,記者提到國務卿魯比奧被問及美國人是不是擁有「正當程序權利」時,認爲當然所有美國人都會享有正當的程序權利。但特朗普對此不以爲然,對美國人是否享有憲法保障的正當程序權利的提問,特朗普表示:「我不知道,我不是律師,我不知道,這樣的要求意味著我們將不得不進行一百萬,兩百萬或三百萬次審訊」。
美國的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了法律的正當程序,意味着一個人面臨刑事指控的時候,擁有某些權利。但特朗普政府完全無視憲法保障的權利,加西亞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如果特朗普那麼喜歡在關稅談判中討論黎智英的話,我們也應討論一下加西亞的個案,因爲把黎智英放在香港的監獄,實在太仁慈了,如果付點錢把他放在薩爾瓦多那樣「有去無回」的超級監獄,恐怕阻嚇性會大一點,香港的工具箱會多一種工具。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