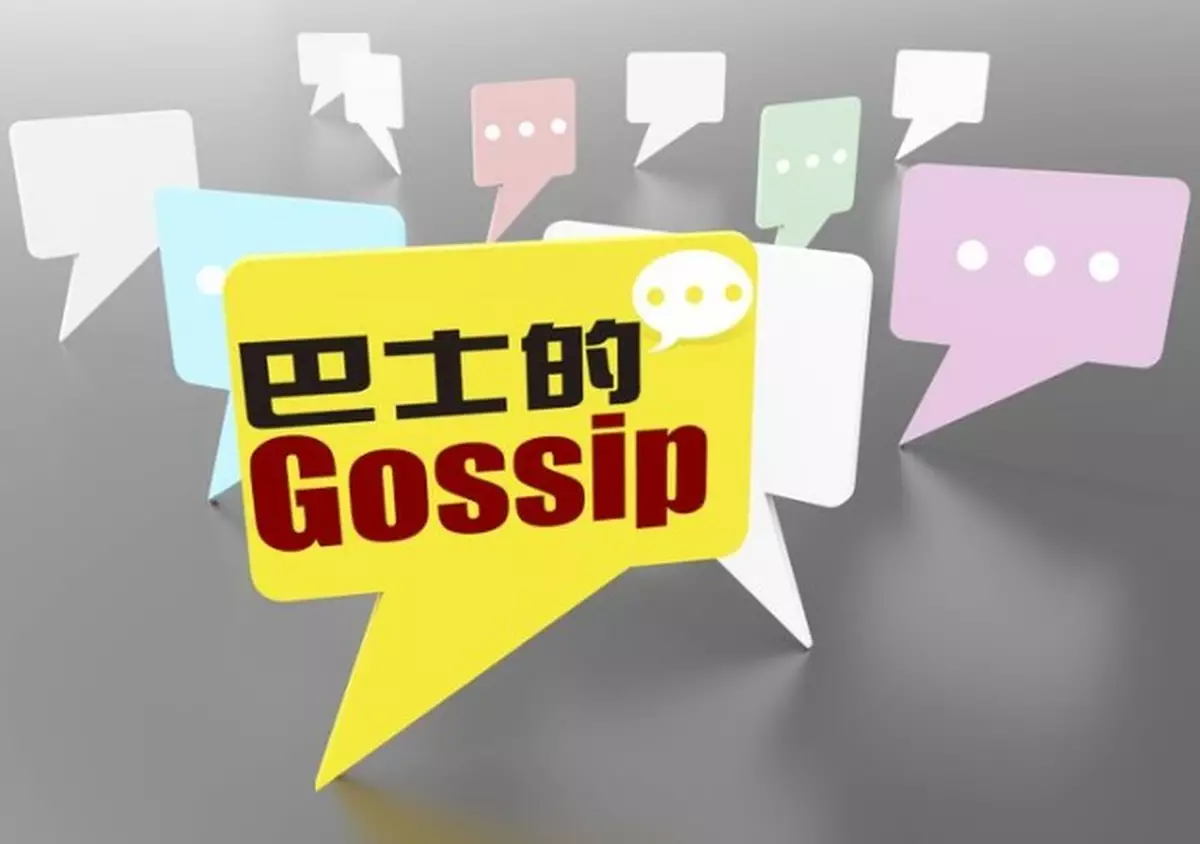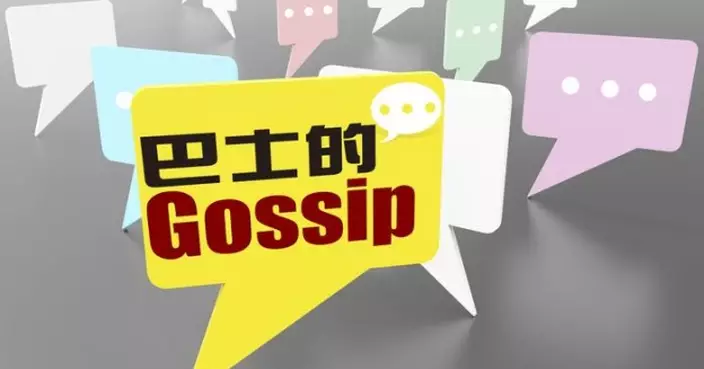恒隆地產有限公司的主席陳啟宗在南華早報撰文,講到香港抗疫失敗,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導力。他認識許多高級官員,問題主要不是他們的能力問題,它更多地與個性有關--特別是缺乏謙遜和過度的毫無根據的自信心。這些是我們一些領導人的終生特徵。
陳啟宗認為,香港與大陸的聯繫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都很重要,但如果不能滿足北京的要求,我們就會被孤立。不幸的是,主要由於當地領導不力,我們基本上是與所有人隔絕的。香港確實是夾在石頭和硬地方之間。
陳啟宗文章全文如下: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的主席陳啟宗在南華早報撰文。
地方領導層的失誤如何讓香港受制於奧米克朗的擺佈
自1997年以來,香港還沒有面對過比大流行病更嚴重的非政治性問題。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及其後果大大損害了人們對我們城市的信心之後,我們處理最新一波新冠的方式讓全球社會產生了更多疑慮。讓我對目前的混亂局面提供一些看法。
為什麼香港必須跟隨中國大陸的 "動態零感染 "戰略?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朝著群體免疫的方向發展?作為一個轉口港和國際城市,我們的經濟福祉既依賴西方,也依賴大陸。
例如,前者是資本的提供者,後者是資本的使用者。交易經常在香港進行。然而,我們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關係還有一個關鍵層面。我們的許多公民每天都要跨越邊境去工作,兒童也同樣要跨越邊境去上學。
換句話說,雖然我們與西方的聯繫主要是經濟上的,但與中國大陸的聯繫是經濟和社會的。香港和深圳之間的邊界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過境點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放寬與大陸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區的旅行限制,對香港來說顯然更為關鍵。鑒於在應對這一流行病的政策上存在分歧,我們只能選擇其中一方。
如果採用 "動態零度 "的方法,我們必須實施嚴格的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關閉我們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邊界。其經濟後果是可怕的,但如果這意味著我們可以自由進入大陸,那麼這應該是值得的。
不幸的是,主要由於當地領導不力,我們未能滿足大陸的要求。因此,我們基本上是與所有人隔絕的。香港確實是夾在石頭和硬地方之間。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中所經歷的,與兩年前西方國家所經歷的並無不同。只是這裡的情況更糟糕,而且有不合理的理由。醫院不堪重負,死亡率很高,市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使我們的情況不合理的是,在2020年,沒有人知道病毒是什麼樣的,也沒有疫苗。今天的情況已經不是這樣了。明顯的事實是,我們的政府沒有勝任地處理這種大流行病,甚至到了今天。
要實現動態零感染有兩個標準。首先,必要的基礎設施必須到位,包括高比例的公民接種疫苗,有效的新病例檢測和接觸者追蹤系統,擴大臨時醫院容量等實際安排,以及與公眾及時、適當的溝通。第二,一旦出現新的病例,政府必須果斷地採取行動。
我們的領導人沒有做到這一點。事實上,他們莫名其妙地抵制了其中許多措施。因此,當高度傳染性的Omicron變體到來時,我們完全措手不及。現在為這一浪潮建立上述的基礎設施已經太晚了,因為病毒已經無處不在。
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領導力。我認識許多高級官員,我認為問題主要不是他們的能力問題。它更多地與個性有關--特別是缺乏謙遜和過度的毫無根據的自信心。這些是我們一些領導人的終生特徵。
也可能有一種相對於大陸的優越感。他們忘記了大陸的表現遠遠好於其他許多大國。中國只有11萬多例新冠病例,死亡人數不到5,000人。美國的可比數字是近8000萬例,超過95萬例死亡。
人們可能會正確地問,一個生命值多少錢。如果我們目前的混亂局面有任何一線希望,那就是讓香港認識到,在許多關鍵的治理領域,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之一。
從長遠來看,人類將不得不學會與新冠共處。這一點我們知道,但未知的是它將如何演變。那些選擇群體免疫方法的人別無選擇,只能面對可能出現的任何更新的菌株。
讓我們希望未來可能出現的任何變種都不那麼致命,但如果它們不是呢?另一方面,中國仍有一個選擇,即繼續以 "動態零 "政策對抗大流行病,或改變方向。
這將取決於病毒的變異方式,以及北京是否能設計出更有效的疫苗。如果Deltacron變體--兩個月前在歐洲被發現,並且被認為像Delta一樣具有致命性,像Omicron一樣具有傳染性--成為下一個主導毒株,北京沒有理由扭轉方向。
就目前而言,判斷還為時過早。由於有如此多的事情需要權衡,在這個問題上,安全要比遺憾好。
那麼,我們在香港應該做什麼?本屆政府還有不到四個月的任期。我們只能希望大流行病屆時會自然消退,這在歷史上並非沒有發生過。有了希望,7月1日起的下一屆政府會更有能力。不幸的是,我們只得等待。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