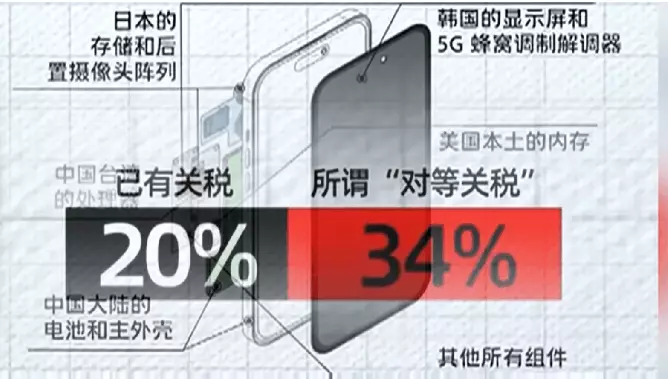李家超,香港回歸後首名員警背景出身的政務司長,近日正式宣佈參選下任行玫長官,旋即得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為代表的建制派各重量級人士的祝福。對此,社會上包括海外輿論有諸多猜測和演繹。
在香港要尋找講政治、有擔當、懂財經、貼民情、有香港故事等不同專長的人才,可以找到不少,但要將這些特性集於一人身上,起碼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完人。因此,在看待某一個事物的時候,絕對不能脫離它所處的大社會背景來分析,否則就會跑題,又或被一葉障目。
要從大環境來分析中央選擇李家超,無非是從外部和內部兩大因素,如符合所需要求,一切就是合理的。
第一因素,我們看國際大環境。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經濟下行,還看不到復蘇的跡象,各國仍處在艱難的時刻。受地緣政治衝突影響,今年又爆發了俄烏之戰,雙方仍在膠著,戰事卻經延伸到美國與北約針對俄羅斯之間的制衡與反制衡,由此引發了“金融戰”、“能源戰”、“糧食戰”等,大國間的政治較量,極大地衝擊了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
我們正面對國際形勢風起雲湧,中美博弈激烈,正處於百年未有大變局之深刻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前不久,美國副國務卿舍曼出席美眾議院聽證會時警告,俄羅斯因為烏克蘭戰事而面對制裁,如果北京向莫斯科提供物質支援,應從俄羅斯現狀(被制裁)中汲取教訓;更甚者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畫近期到臺灣搞事,公然挑戰中國對“臺灣”問題的紅線;總統拜登多次指中國才是美國的最大對手,決意加快推進“印太戰略”。這一系列對中國的“招惹”,是來者不善,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
香港作為中美博弈的前沿,與美國無論是政治人脈、法律體系、關聯企業以及資本往來,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任何一絲風吹草動,都會掀起百丈風浪。
過往,香港是內地引進外國資金、經濟人才、科學技術等的主要通道,但在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下,有關引進已被美國單方面悄悄放下閘門;不少外資企業和人才以“防疫過嚴”為由,陸續撤離香港。這些充分體現美國對香港的干預從未停止,只是在2019年“黑暴”後,他們從後臺走上前臺,由代理人到直接操作,未來涉及國家主權、核心利益的挑戰不會停止。
香港第一責任人在面對國家安全被挑戰時,必須要有堅定意志和勇於擔當,常懷危機意識,才能為中央守好香港的安全大門。從這個角度思考,挑選經歷過政治風波、打過硬仗的李家超任下屆行政長官,屬於預料之中。
第二因素,我們看香港的社會矛盾。受2019年“黑暴”政治鬥爭的影響,雖然中央制定了《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但政治氣候和意識形態仍然分歧。同時,這兩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特別是第五波疫情如同海嘯般衝擊,主要經濟活動幾乎停擺,長期累積的貧富懸殊、土地房屋、教育醫療等社會深層次矛盾亟待化解。特別是這次疫情暴露出香港百病叢生,現屆政府又一再錯過發展機遇期,管治停留在各類“宏大”規劃以及每年的施政報告宣讀中,市民沒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社會怨氣極大。
如何化解矛盾,平復社會情緒,新特首需要做的是在“一國兩制”下,履行好特首雙責任制,既向中央負責,心懷國家;也要向特區負責,人民至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管治者提出“五個善於”,除了提出特區管治者要擔當起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外,也要承擔起解決香港經濟民生的主體責任。
香港管治難,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經常受制於各種既得利益的拉扯,這些利益集團控制著香港部分重要資源和人才,經常有持無恐地要脅政府分割利益,霸佔重要公職為其服務,導致政府應該做的事、想做的事,做不成或做不好。以房屋問題為例,覓地建屋觸動了利益集團的肥肉,他們採取封盤、環保、提價,甚至要把上任敢於拓地建房的特首拉下馬等手段,目的就是要阻止政府解決市民最迫切的房屋問題。因此,政府施政必須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特首需要聆聽各方意見,但不能任人擺佈,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推進。
特首換人,政府可以重組,既得利益集團一定會想方設法,爭取和施加他們的影響力。因此,選擇下任特首,應該是各方都可接受,而且與利益集團保持適度距離,才有空間推動下屆政府大刀闊斧厲行改革。在一定意義上,特首不但是維護政府機器正常運轉的執政者,也應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改革者,帶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再出發。
外界認為李家超過往工作經歷比較單一線條,人脈圈子相對較窄,可否具備駕馭一個厐大而複雜的政府機器的能力?我認為,這或許正是他的優勢,結交“圈子窄”可以不受各大利益集團的牽扯和羈絆,可以更有為地推動社會改革。從他組成競選班底看,集中了前兩任特首的支持者,向社會釋放出團結、凝聚社會力量的積極資訊。從這個角度看,李家超成為下任特首,也是中央選人的一個重要考量。
作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昇基金董事 周春玲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