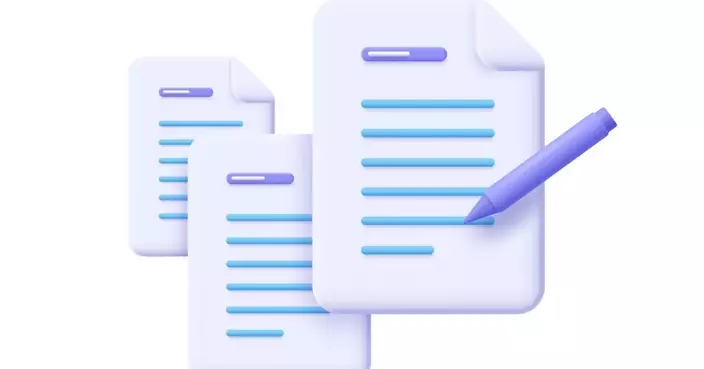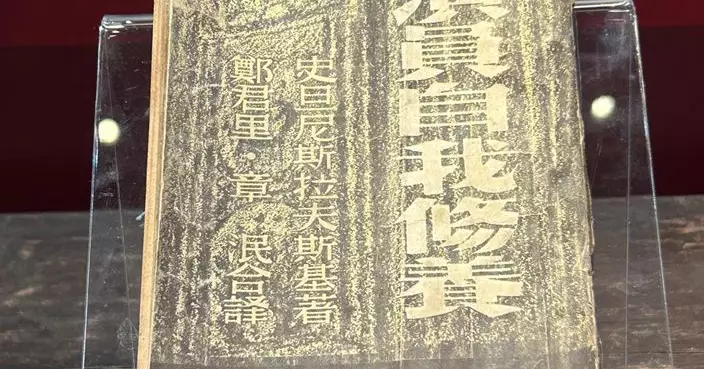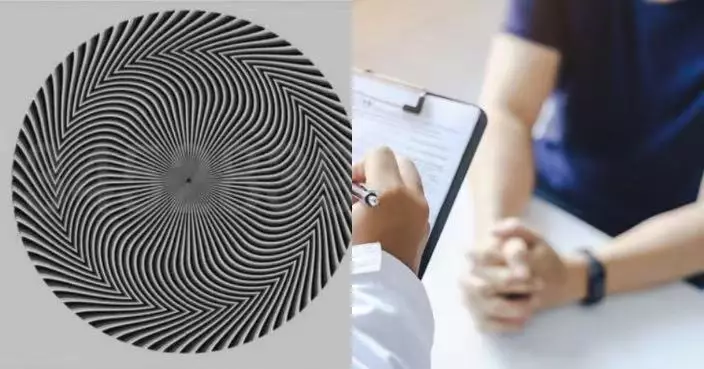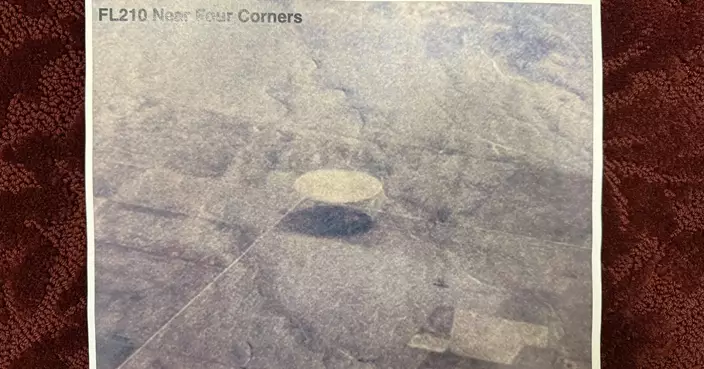近日,香港地產巨頭長和系拋售港口資產的消息引發熱議,表面是資本的「戰略調整」,實質卻是百年買辦基因的歷史重演。從殖民時期的鴉片販子到今日的壟斷財閥,從依附洋行到跨國套利,香港的買辦資本從未真正擺脫「經濟附庸」的底色。當某些人高呼「在商言商」時,我們必須清醒追問:這究竟是懸崖勒馬的覺醒,還是一條黑路走到底的執迷?
歷史輪迴:從殖民買辦到跨國套利
19世紀的香港買辦,靠著代理英資洋行、壟斷鴉片貿易起家,以「中間人」身份榨取華人血汗;今日的資本寡頭,趁當年香港即將回歸「契機」,翩然成為英國新的代理人,則以「國際化」之名,將港口、基建、民生命脈包裝成金融商品,向全球資本拋售套現。二者手法雖異,本質如一:將國家與市民利益置於跨國資本的賭桌之上。
毛主席早已看透買辦資產階級的寄生性:「他們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當年的買辦依附東印度公司,今日的財閥則擁抱華爾街基金;當年的利潤靠鴉片與苦力,今日的暴利則來自地產霸權與金融投機。歷史從未終結,只是換了一副面具。
經濟主權之爭:誰在掏空香港的根基?
香港的繁榮,本應建基於服務國家所需、紮根民生所急。然而,某些資本集團卻將「自由市場」扭曲為「自由掏空」—— 掏空產業,棄實業而逐地產,拋技術而炒樓市,導致香港工業空心化,青年淪為地產金融的螺絲釘;掏空民生,壟斷民生行業坐地起價,從電力到超市,從碼頭到藥房,市民血汗成了壟斷利潤的燃料;掏空公義,就如當年以「官商協作」之名、「紳士、爵士」之頭銜、尊貴議員之席位作政治尋租(如獲低價批地、專營權先),在回歸後以「諮詢」「顧問」等渠道,將資本欲望包裝成「專業意見」,左右公共資源分配。以更隱性的勾連,美其名為「依法遊說」,實質是以資本綁架公權,使政策淪為壟斷利益的遮羞布;掏空主權,將戰略資產(如港口、電訊)出售予外資,等同將國家安全與經濟命脈交予他國之手。
毛主席曾一針見血指出:「買辦資產階級與反動政權勾結,是剝削人民的兩把刀。」當土地規劃向地產利益傾斜、公共服務被寡頭壟斷定價時,基層市民的「荷包」與「飯碗」,便成了資本與權力交易的犧牲品。 毛主席也警告:「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勾結,是中國人民的死敵。」今日某些資本的跨國套利,何嘗不是對「一國兩制」下香港主權的隱形侵蝕?
懸崖勒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示
新中國成立之初,共產黨以雷霆之勢沒收官僚買辦資本,將其轉化為國有經濟的基石。這不是「仇富」,而是終結剝削、捍衛主權的歷史正義。鄧小平先生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強調的是「市場」與「社會主義」的辯證統一:市場活力需釋放,但資本絕不能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
反觀香港,部分財閥至今未改買辦思維。對國家,口頭「愛國」卻熱衷離岸註冊,一邊享受「一國」紅利,一邊規避「兩制」責任;對社會,高調捐款塑造「慈善家」形象,卻無視基層住劏房、青年無出路的結構性壓迫;對大義,在中美博弈中左右搖擺,將資產變現為「全球化」賭注,隨時準備棄船而逃。 這種「經濟騎牆派」,與當年何東家族既效忠港英又周旋國民黨的「雙面忠誠」何其相似!
出路何在?破除壟斷、還富於民
香港要打破買辦資本的百年詛咒,必須敢於直面四大課題:一、強化國家意識。經濟主權是國家主權的延伸。對關鍵領域(金融、能源、交通)的外資滲透,必須設立「安全紅線」,防止香港淪為跨國資本的提款機。二、終結地產霸權。參考內地「房住不炒」經驗,以公屋為主體、市場為補充,打破地產財閥的定價壟斷,將土地利益回饋全民。三、推動產業革命。善用國家每五年「規劃」與大灣區機遇,以國資引導科創投資,培育本土實業,讓青年擺脫地產金融的宿命輪迴。四、斬斷權錢紐帶。強化公共決策透明度,打破利益固化並以「旋轉門」身份介入政策制定;建立資本「紅綠燈」制度,對涉及民生、戰略領域的投資,必須要有社會效益審查;推動反壟斷立法,打破「大財團立法、小市民守法」的扭曲格局,讓市場迴歸服務社會的本義。
歷史的審判從不缺席
回顧歷史,並不是要清算後殖民資本家的買辦基因及其「罪惡」,而是要認清時代和形勢。香港回歸不可能再容許買辦資本家的存在;洗涮百年屈辱、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不可能再有買辦資本家生存的土壤。買辦資本家必須隨著打倒帝國主義、殖民侵略而消亡。
從晚清盛宣懷到民國四大家族,從港英何東、利希慎到今日財閥,買辦資本的結局早已註定:當其掏空國家、背離人民之時,便是歷史審判降臨之日。某些人若仍執迷於「黑路」,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唯有將資本融入民族復興的大潮,方是正道滄桑。
懸崖勒馬,猶未為晚!
作者:吳秋北(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
來論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