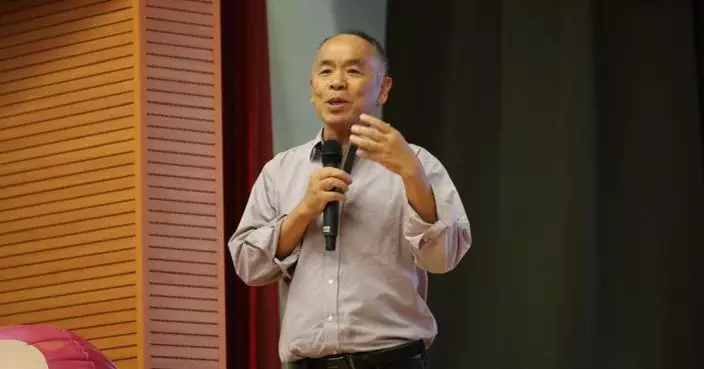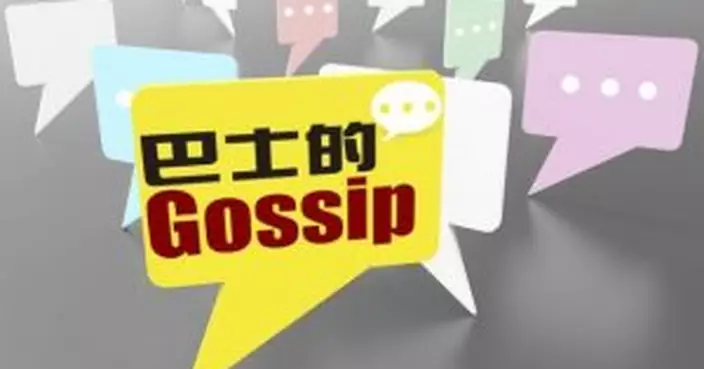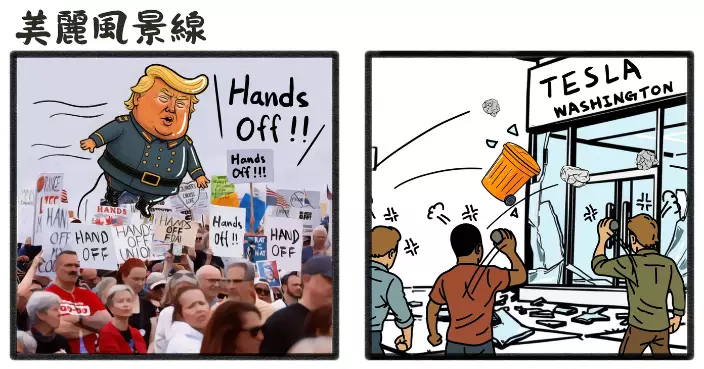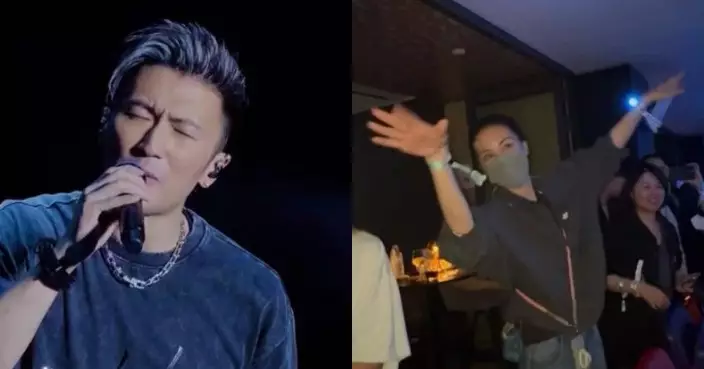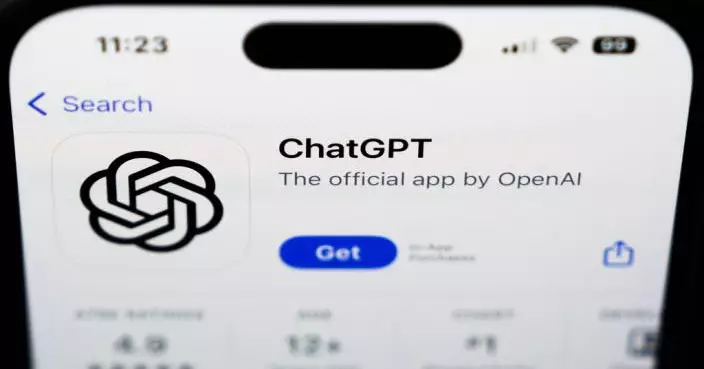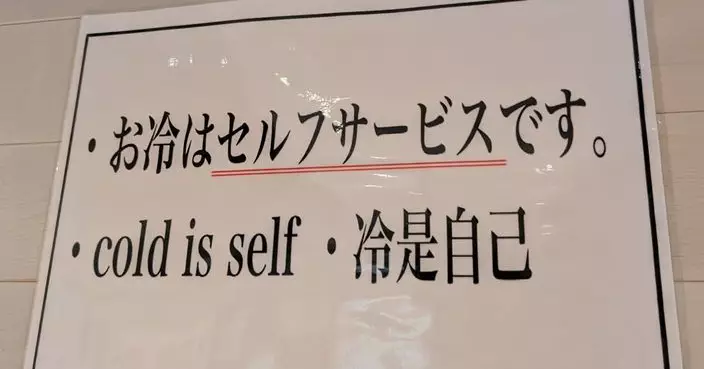樂施會發表《香港貧窮狀況報告 2024 逆境下的出路:以轉變迎接改變》,分析政府統計處數據,發現今年第一季度的香港整體貧窮率達20.2%,逾139萬人處於貧窮狀態。疫情前後的貧富差距由 2019年的34.3倍進一步擴大至2024年第一季的81.9 倍。

圖:樂施會總裁曾迦慧(中)表示據政府統計處第一季數據,本港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巴士的報記者攝)
最貧窮家庭月入中位數僅1,600元
樂施會總裁曾迦慧表示,以政府統計處2019至2023年及今年第一季數據,分析按十等分組別劃分的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在今年第一季,最貧窮一成住戶的家庭月入中位數僅1,600 元,較疫情前大跌超過五成(54.3%)。相反,最富裕的一成住戶家庭月入中位數達 131,100 元,較 2019年上升近一成,两者差距達 81.9倍。

圖:樂施會發表2024《香港貧窮狀況報告》(巴士的報記者攝)
獨老和雙老貧窮住戶佔26萬
樂施會港澳台項目總監黃碩紅指出,香港貧窮住戶數目在今年第一季增至61萬,佔整體住戶 22.7%。與2019年相比,本港貧窮獨老住戶數目更大幅上升47.2%,達到131,700戶;貧窮雙老住戶亦上升了55.3%,達到 132,800戶。

圖:港澳台項目總監黃碩紅(右)指獨老和雙老貧窮住戶大增(巴士的報記者攝)
疫後復常第二年,本港65歲或以上的貧窮長者人數超過58萬,當中超過558,900貧窮長者為非經濟活躍人士,兩者都較2019年急增42.9%。與此同時,本港現時長者勞動參與率僅為13.9%,較内地的25%及挪威的 22%為低。
促政府實踐真正「積極老年」
樂施會研究及倡議經理梁名峰博士表示,疫後經濟復蘇不似預期,是貧窮惡化原因之一,但強調人口老化並不必然導致社會危機,若社會各界能朝向積極老年(Active Aging) 的目標一同去營造一個長者友善的生活環境,特别是善用科技及社會創新的方法回應基層長者的需要,同時政府應提供足夠到位的政策誘因,為仍有志有力的長者『賦能』,創造投入社會及勞動市場的機會,長者也可成社會的重要資本。」

圖:研究及倡議經理梁名峰博士(左)表示疫後經濟復蘇不似預期是貧窮惡化原因之一(巴士的報記者攝)
樂施會提出多項建議
為此,曾迦慧透露樂施會提出多項扶貧建議,包括在貧窮線下實現精準扶貧 加入「賦能」及「積極老年」等目標。另外,透過「官商民」合作,孕育更多具社會影響力的創新項目,回應不同貧窮群組的需要,以發揮更大的社會貢獻。
推動積極老年 (Active Aging)
曾迦慧又建議成立「獨老及雙老長者住戶資料庫」,以掌握長者實際情況,並擴大「支援長者及照顧者先導計劃」至 18區,提供針對性探訪、情緒支援及轉介合適的社會服務等。
改革中高齡就業計劃提升就業率
現時中高齡就業計劃的申請手續繁複或令申請者卻步。樂施會建議,當局應簡化僱主申請計劃的程序和條件,並直接按新聘請的年長員工人數發放津貼。僱主只需提交員工的聘用及出糧證明,即可獲發津貼。
善用科技創新基層醫療
針對有照顧需要的長者,政府可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以遙距醫療等科技為長者提供適切及便捷的醫療及保健服務。在日常保健中,政府亦應推廣適合長者的運動,如跳舞防跌、拉筋等,更可結合科技透過線上平台鼓勵長者居家自主訓練,同時可考慮擴闊醫療券的應用範圍至促進健康的運動線上線下課程。
創造彈性工作機會提升幸福感
現時「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供不應求,平均輪候時間長達9個月,當中以膳食服務、護送及一般家居或家務服務最受歡迎。樂施會建議政府可資助更多非牟利機構開設相關服務,並提供彈性工作安排予相關獲聘員工,吸引未能從事長時間工作的非經濟活躍人士(如家庭照顧者或有能力的長者)投入相關職業,同時可加快居家安老服務的輪候時間,改善長者生活質素。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一名日本男性因沒有穩定工作遲遲未能組織家庭,加上自己需獨力照顧有認知障礙症的母親,他指自己屬於社會上的「弱勢男性」,並詢問「誰能來拯救自己」。
有經濟學碩士學位 卻未能成為專職教師
改名日本男子在首都圈的兩所大學擔任兼職講師。他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曾多次發表論文並在學術會議上發布成果,但始終未能成為專職教師。
「即使進入最後一輪選拔,也是其他人被選中,這種情況在30至40多歲時曾發生過兩三次。我在國外的大學當過客座教授,也擁有指導學生的經歷……」

AP圖片
住父母家 需照顧患認知障礙症母親
他每周上5節課,加上在專科學校的集中授課,年收入250萬日元左右(約13萬港元)。由於從4月開始課時將減少,預計收入將減少大約80萬日元。但是,他上研究生院博士課程時的助學貸款還有200萬日元有待償還。
他住在父母家裡,不用付房租,但八年前母親得了認知障礙症。被認定「需要一級護理」的母親,每周可以享受兩次日托服務和一次兩天一夜的短期托養服務。但是,由於無法依靠別人來護理母親,他周末和夜間很難外出。原本用來補貼生活費、受市民團體委托的講座也無法再進行。學術會議本是與其他研究人員建立人脈的機會,現在也無法再參加。
姊弟責怪洞察不到父親病情
「我想,母親明明知道自己得了認知障礙症,為什麽能做的事情卻做不了呢?有時我甚至會怒吼。」
照顧母親是一種長期的壓力,但他與原本可以分擔的姐姐和弟弟卻處於斷絕關系的狀態。
十多年前,他父親被診斷出癌症時,姐姐和弟弟責怪與父母同住的他「為何沒有注意到」病情。父親去世後,圍繞遺產繼承問題,他被姐姐和弟弟要求離開父母家。

示意圖
「我想,姐姐和弟弟認為我一邊當著兼職講師一邊住在父母家,是靠父母養活或者一直遊手好閒,所以爆發了不滿吧。」
兩人都知道母親得了認知障礙症,但沒有幫忙,而是由這名男子一手承擔護理工作。
聲稱沒有穩定工作找不到結婚對象
「如果我有配偶或孩子,可能還會互相幫助。但是,我沒有結婚。」他並不想一直單身。20年前,他曾參加了兩年左右的相親活動,「進展不順的理由總是一樣的,歸根究柢還是沒有穩定工作。」
母親的認知障礙症症狀每天都有波動。「即使我很努力,她的症狀也不會好轉。可能這種狀況還會持續很多年。」不知道假牙放在了什麽地方之類的小事,也會在精神上把他逼入絕境。
存款很少 無法送母親入住護理機構
雖然想過早晚讓母親入住護理機構,但因為存款很少,經濟上有困難。買東西或散步的時候,看到母親和鄰居聊天的樣子,心中也會猶豫,覺得將她送入護理機構「也許會剝奪她的樂趣」,所以還不能下定決心。

示意圖
中老年男性困境易被忽視
關於「弱勢男性」的定義,作家托伊安娜列出了16個類別,上述男子屬於其中的「護理者」和「非正式員工」。
他每周會去做一次針灸,與針灸師聊天以及在社交媒體上與朋友交流成為他的精神慰藉。有人對他說「你真不容易」,這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安慰。
但是,他有時也有這樣的感覺。「與女性的貧困相比,像我這樣陷入困境的中老年男性的實際狀態,社會上應該沒有多少人認識到吧?」
日本正在推動「多重支援體制建設事業」,以幫助那些不管處於什麽狀況和年齡、面臨著僅靠一個支援機構難以解決問題的人們。
在這名男子居住的地方,政府也設有諮詢窗口,但他從未利用過。因為他覺得,「我說了也沒人會理我。」
「今後像這名男子一樣的人可能會增多。」專門研究「冰河期世代」(即一般指出生於1970至1982年,經歷了日本1993至2005年「就業冰河期」的一代人)問題的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下田裕介警告。

示意圖
因經濟狀況放棄結婚 單身者居多
冰河期世代的主體,現在是40多歲,年紀大一些的是50多歲的中壯年。這些人今後將面臨照顧父母的問題。
正式員工的道路走不通,只能以非正式員工身份工作。經濟上沒有積蓄,還要照顧父母……對於冰河期世代來說,這名男子的經歷絕非個別例子。
據下田介紹,冰河期世代與泡沫一代(一般指1986至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時期參加工作的一代人)相比,正式員工的實際工資水平每月低7萬至8萬日元,儲蓄不足100萬日元人群的比例也較高。由於經濟原因而放棄結婚的人不在少數,單身者居多也是一大特點。
建議國家及行政部門營造環境與提供支持
下田認為,當務之急是國家和行政部門營造環境和提供支持,以便這些人既能照顧父母又能兼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