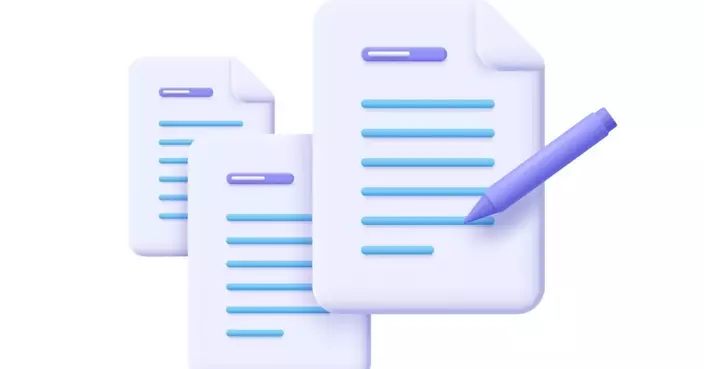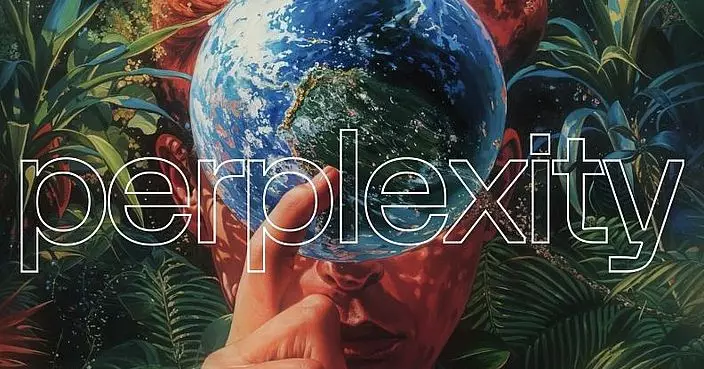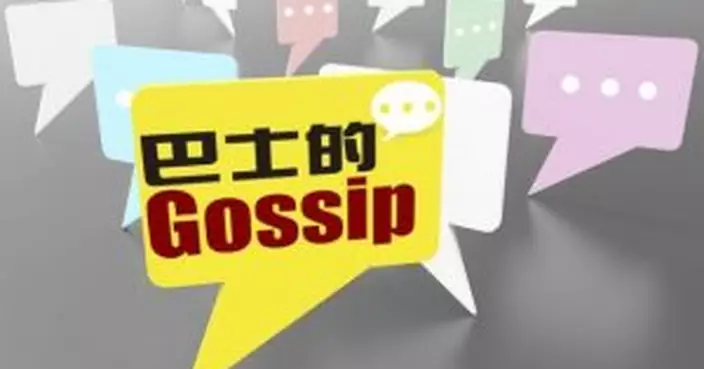香港立法會全票通過23條立法。這是一個歷史性時刻,香港回歸26年,終於補齊有關國安立法的最後一塊拼圖,築牢保障國家安全的屏障。
過去香港人並不覺得香港有什麼國安挑戰,亦不覺得香港會出現動亂,所以對23條立法,只看到其限制自由的一面,而看不到保障安全穩定的另一面。但過去十年,香港發生的動亂,就令大家明白保護國安的必要性。
政治穩定就好像空氣一樣,當它存在的時候,你並不覺得有何寶貴,但當失去的時候,才知道相當致命。假如10年前香港已經有現在的23條立法,特別是不可以像2003年那種剝牙版23條立法,香港或許不一樣。
第一,2014和2019年的事件不易發生。本地的反對力量在外部勢力推動下,過去10年,反政府攻勢不斷升溫。10年前2014年,反對派透過大規模的非法上街佔領,阻斷了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道路,企圖逼使政府在政制改革上,大幅讓出政治權力。2014年的佔中是反對運動的第一次跨越,由遊行示威跨越到大規模的非法佔領。
到2019年是第二步的跨越,由非法佔領跨越為大規模極端暴力事件,滿街滿巷掟汽油彈,放火燒人,毆打不同政見者,反對運動的暴力性快速推向高峰。以當年12月8號和所謂屠龍小隊相關的恐怖襲擊事件為例,完全是一宗有設計的殺警恐襲,以圖引發大規模暴亂,幸好警方及時破獲制止。
這些大規模的群眾暴亂,背後涉及大量的金錢支撐,近日暴露出來本地政團直接收美國政府屬下機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贊助有之,透過一些有錢的中間人間接收錢亦有之。總之,資金源源不絕,只要你夠膽激進地反對政府,大搞顛覆活動,就不愁資源短缺。
如果10年前已經有現在23條立法的「境外干預罪」,恐怕這些外地勢力的干預不至於那麼明目張膽,本地有錢中間人和政團,亦不能公然轉移政治資金。水源不到,或許2014年和2019年的事件就不會發生。
二,黎智英沒有那麼猖狂。黎智英案暴露出來的狀況,可以說是去到驚心動魄的地步。《蘋果日報》的高層如社論寫手楊清奇就直言,《蘋果》只有「鳥籠式編輯自主」,實際上是黎智英「話晒事」。而《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在辯方追問《蘋果日報》有沒有編輯自主的時候,亦都笑稱「如果黎生冇出聲嘅時候都係」。
黎智英毫不忌諱在自己控制的媒體,大力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大陸,亦全力散播挑動港人非法上街和肆意攻擊國家言論。
如果10年前已經有23條立法,煽動罪罰則更高,勾結外國勢力發表煽動性刊物會有10年的刑期,或許黎智英沒有那麼猖狂,就沒有那麼多人被煽動出來作亂。
三,示威者沒有機會誤入歧途。如果大家有看過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1895年的著作《烏合之眾》,就知道群眾很多時都是盲目的,在街頭運動激情澎湃的時候,理性放在一旁,示威者不單闖入議會,圍毆途人、放火燒人、刺殺警察,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事過境遷,示威者被送上法庭,就要面對嚴苛的刑罰,但悔之以晚。如果10年前有23條立法,特別是制止境外勢力推動香港反對運動,示威者沒有跌入激情澎湃的抗議環境中,最後或許可以免去牢獄之災,不用讓大好青春在獄中虛度。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現實世界沒有「如果…」,只有未來。23條立法早一日比遲一日好,早一日填補了國安的漏洞,早一日令香港不會成為美西方攻擊中國的突破口,對國家、對香港都是一件好事。
盧永雄
中國人爲特朗普改了一個混名,叫做「川建國」,實在難以想像特朗普執政才100天,就會對中國做出這麼大的貢獻。
加拿大選舉剛剛結束,本來執政自由黨在上任總理杜魯多領導下,向特朗普叩頭,搞到民望急滑,不過接任的卡尼「冷手執個熱煎堆」,乘着特朗普壓逼加拿大成爲美國第51個州的風頭火勢,強硬回擊。結果加拿大人同仇敵愾,重新支持自由黨,令卡尼勝選。
這個戲劇性的轉折,或許從加拿大人買咖啡的習慣已經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最近痛恨美國,將「美式咖啡」改名爲「加式咖啡」,抵制美國的Netflix和迪士尼,取消到美國旅遊的計劃,甚至沽售在美國擁有的渡假房產。相信加拿大人現在也開始明白,當日緊跟美國對中國電動車實施100%的進口關稅,是傻得很徹底的行爲。
特朗普的殺傷力,從一個民調已經看到。據調查公司IPSOS最近公布對29個國家共2萬名成年人的調查顯示,環球受訪者認爲「美國對世界事務總體上有積極作用」的人數比例,從半年前的59%急降13個百分點到46%;相比之下,中國就在同一份報告中首次超越美國,從半年前有39%受訪者認為中國對世界的總體事務有積極作用,急升到49%。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調查在3月21日至4月4日進行,特朗普在4月2日開始向全世界徵收極其離譜的超額關稅,但調查未能反映之後環球洶湧的民情。如果現在再進行同樣調查,恐怕中國領先美國的百分比將會更高。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伊(Joseph S. Nye)提出的一個「軟實力」的概念,奈伊曾任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深明美國操控全球之術。他認為自冷戰以來,美國除了靠軍事和經濟的「硬實力」領導全球之外,還懂得用「軟實力」讓全世界折服。美國有讓世界艷羨的科研能力,長期標榜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向世界輸出美式流行文化,這就是美國真正的實力泉源。
不過特朗普上任100天,就完全摧毀美國的「軟實力」。在世人的眼中,美國不僅沒有變得更加偉大,她的商品服務以至於文化,就成爲過街老鼠,特別是在盟友中的厭惡感尤大。由於美國對親密的朋友也肆意霸凌,在上述民調的29個受訪國家之中,對美國印象較好的反而是南美洲或者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那些認爲美國對世界總體事務擁有積極作用的人數少於40%門檻的國家,反而是美國的緊密盟友,包括英國、意大利、愛爾蘭、澳洲、西班牙、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典、荷蘭和加拿大。
特朗普在這場關稅當中,叫全世界的國家來跟美國談判,去「親吻我的屁股」。當世界各國面對霸凌顯得又怕又怒、彷徨無助之際,中國就選擇和美國硬扛,反加美國關稅。中國外交部4月29日在公衆號發布中英文的重磅視頻,題爲《不跪!》,強調面對美國關稅打壓中國不跪,「因爲我們深知中國不退,弱國的聲音就有人傾聽,霸權的欺凌就有人阻擋,世界的公理就有人守護」。
外長王毅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出席金磚國家外長會議的時候,狠批美國拿關稅作籌碼,向國家漫天要價,如果選擇默不作聲、妥協退出,只會讓霸凌者得寸進尺。王毅呼籲金磚國家共同反對一切形式的保護主義。
中國已經成爲全球反抗美國關稅霸權的先行者,發動全球南方國家和美國抗爭。有歐洲外交官私底下也表示,對中國強烈反抗美國的關稅霸凌十分讚賞,認爲只有中國才夠膽這樣做。其他國家在中國起來反抗之後,就採取觀望態度,和美國的談判時也採取拖字訣,不談怕惹怒美國,但是談的時候也不具體還價,談完和沒有談一樣。
國際社會就很像一個森林,不但比拼硬實力,還在比拼軟實力,不但比拼國家的力量,還比拼國家領袖的領導力,以及國民的堅韌性。
如今在中美第一回合的比拼中,美國這個惡霸就顯得相當無助,遇上中國的強硬反擊,遇到中國外交部發布《不跪!》的影片,連特朗普都選擇避而不戰,改爲由財長貝森特出來為特朗普執政100日總結,聲稱他得的數字是貿易戰會令中國1000萬人失業。不過,這一套靠嚇的話術,現在已經顯得蒼白無力,中國有意和美國硬扛下去。在這場軟實力的血拼中,中國已佔盡上風了。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