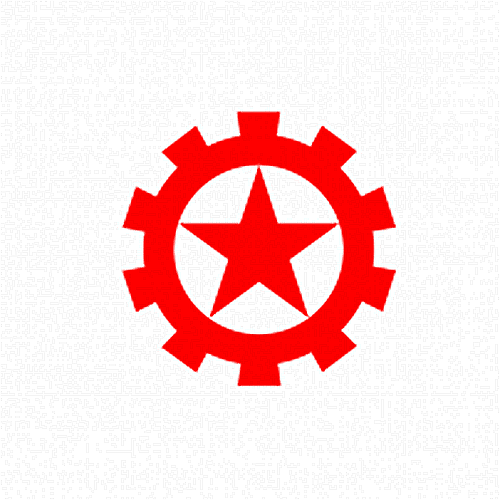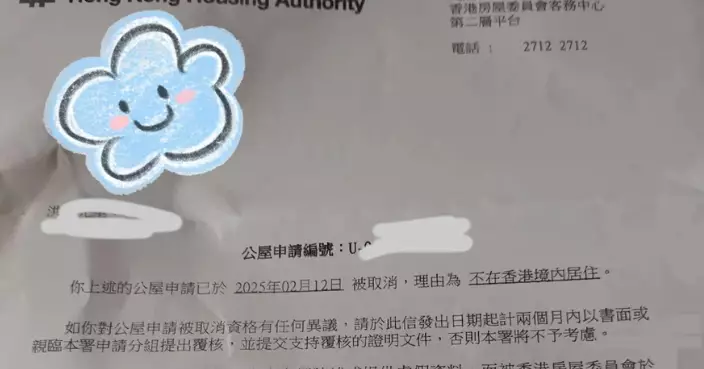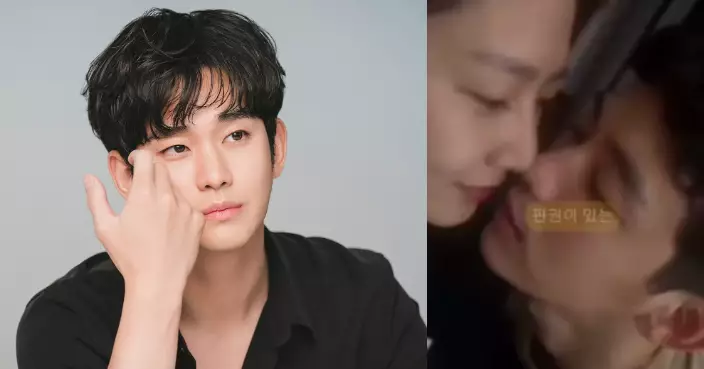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的資料,公屋存在的目的,是「為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負擔的租住房屋」。只要擁有在港永久居住的資格,同時符合由房委會制訂的入息及資產要求,經過一段輪候時間,便可以獲分配一個單位,享受由以公帑支持、價廉物美的公共房屋。
雖然公屋住戶只是租客,不具備擁有或買賣單位以享受其資產價值的資格,但是隨著過去十多年私人樓宇價格急升,非常人所能企及;而新建成出售資助房屋數量又偏少,遠遠未能滿足夾心階層的需要,不少市民都退而求其次,「各出其謀」以求獲編配公屋單位。例如公屋聯會前主席王坤便在受訪時提到有年輕人為了避免超過公屋入息上限而放棄晉升和增加薪酬的機會,也有夫婦為了符合申請資格而無奈地使其中一人離開職場;甚至有志願團體發現,近年年輕、高學歷的露宿者的比例不斷增加,正是由於這些初出茅廬的社會新鮮人無法負擔在私人市場租屋的高昂費用,只好露宿街頭以等待編配公屋單位的一日。可見,愈來愈多市民為求得到價格廉宜的居住環境,作出扭曲個人及家庭正常發展的行為。
另一方面,由於公屋只是考慮申請人是否擁有永久居留權及入息和資產是否在上限以內,因此不少土生土長的青年人縱然居住情況困難,例如忍受私人市場高企的樓價或租金、與家人居住在狹窄的生活環境等等,但是由於收入水平高於要求,因而難以享受公屋資源及其帶來的好處。同時,他們往往質疑在苛刻的申請條件下,政府的房屋資源無異於傾斜在普遍學歷和收入水平較低的新來港人士的身上,對港人的慘況則漠不關心。事實上,數據顯示,近年新移民佔公屋新申請個案的比例不足20%,但是部分市民對於「公屋是為新移民而設」的偏見仍然揮之不去,造成土生土長港人與內地移民的關係緊張,甚至成為政治對立和社會情況不穩定的根源之一。
以上所說的現象,不禁令人對公屋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的目的是否有效實現產生懷疑。說到底,對公屋有需要的市民要麼「自降身價」,要麼望門興嘆,正是因為被不合理的入息門檻所難倒而引致。
公屋入息限額機制的四個不合理
房委會轄下的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是負責檢討和建議公屋申請人入息和資產上限的機構。而這個機構所作出的決定,則是根據資格檢討機制而制定。這個機制的計算方法分開兩個主要部分,一是住屋開支,一是備用金。在住屋開支方面,則可以再細分為「住屋開支」與「非住屋開支」,前者的計算重點是「參考租金」,即與公屋面積相若的私人單位每平方米的租金,而後者的重點則是「消費開支」,即按照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其開支水平屬於較低的50%組別中平均的開支費用,再乘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或名義工資的變動(以較高者為準)。至於「備用金」的計算方法,其實就是計算以上一系列因素的「住戶開支」部分後,再抽取其金額的5%。
由運輸及房屋局在3月呈交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有關2021-22年度檢討入息及資產限額的文件中,就指出由於一人單位的參考面積為15平方米,而每平方米的平均租金升至409元,因此住屋開支的部分就是6,135元。至於非住屋開支,雖然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下降,但是名義工資則輕微上升。在兩個指數之中選用較高的一個的計算原則下,非住屋開支的金額同樣有所提升,增至6,186元。在考慮住屋及非住屋開支,再加上根據住屋開支金額而定的備用金,就得出一人申請者的入息上限,在扣除強積金供款後為12,940元。
表面看來,這個機制較全面地參考低下階層的兩個主要能力,即消費能力和租屋能力,再加上備用金一項以顧及申請人的不時之須和儲蓄需要,作為調整入息限額的條件。然而,現實的效果是,由於對申請人收入的考量嚴重不足,所以實際情況與大眾的能力和期望嚴重脫節。例如,就算疫情重創本港經濟的2020年,香港打工仔女的月入中位數依然高達$18,400,意味著在房委會的申請資格機制下,無論有否住屋需要和壓力,都有多於一半的市民不可能申請公屋。加上自2011年起香港正式推行最低工資,連從事低學歷、低技術工種的勞工,如保安、清潔等,月薪高於房委會機制下之水平的人士亦多不勝數。當大部分市民以及基層勞工都無法受惠於公共房屋的資源,難怪容易使人產生「公屋並非給予港人居住」的印象。
此外,以消費作為收入限額的其中一項重要考慮因素也不合理。住戶開支的多少,往往與家庭結構,例如年齡、性別、身體狀況、習慣等相關。比方說,一個父母雙全且有兩名幼年子女的四人家庭,其家庭開支則可能較兩名已屆老齡、且有身體毛病的父母及兩名成年子女的家庭的開支為少。因此,機械性地估算不同人數的家庭所需開支,並為其入息設限的實在欠缺彈性。無疑,「消費貧窮」是其中一種國際主流衡量一個家庭貧窮狀況的指標,但是當香港的扶貧委員會或「居者入其屋計劃」的入息限額都不考慮與消費能力有關的因素,偏偏只有申請公屋時才刻意放大其重要性時,除了因為避免過多考慮收入因素以方便壓低入息限額之外,實在令人難以聯想到其他更好的理由。
另一方面,雖然機制中的住屋開支部分與私人市場的同一面積單位的租金水平掛勾,但是這種做法導致兩個問題的出現。第一,參照對象的條件必須是「同等面積」,但是各個家庭人數的應有面積,全是由房委會在參考私人市場情況後自行決定和調節。例如2003年時,一人單位參考面積是16平方米;至2009年,單位參考面積已經調整至15.3米,到了2021年有關數字更下降至15平方米。因此,即使十多年來租金上升幅度飛快,但是隨著租住私人單位的市民因應負擔能力而「愈租愈細」,房委會也索性「搬龍門」,收縮每個申請家庭人數的參考面積,致使機制下的住屋開支不能準確反映在合理家庭人數應住面積下現實租金的變化及降低每個申請人的居住質素,進而影響申請人收入限額門檻的正當性和有效性。
第二,雖然公屋是為難以在私人市場負擔居所的低收入市民而設,但是私人市場的平均租金在整個申請資格機制中只是佔據其中一個部分,於是就會出現參考租金與申請人收入限額的比例失衡的問題。其實,按照目前的資格限額機制的計算公式,已經注定住屋開支的部分在收入限額中佔據較大的比例。因為公式內只有3個變項,就是住屋開支、非住屋開支和備用金,而由於備用金只是佔5%,意味著前兩者的比例在正常情況下應該佔比40%以上。以2021年的計算方法為例,一人單位的入息限額是$12,940,而住屋開支是$6,135,租金與收入佔比便為47.4%。這套公式背後的意義,就是在房委會的眼裡,只有租金與收入佔比在40%或以上,且收入符合限額以內的基層市民,才算是對「有住屋需要的」的申請人。可是,40%至47%的租金與收入佔比,不單止遠比由政府統計處在2016年進行的《中期人口調查報告》中全港平均租金收入佔比的30%為高,亦比由關注基層聯席的調查所得出的、各種人數的貧窮家庭租金收入比例中位數為高(34.6%至43.3%不等)。可見,房委會的公式設定準則是一套非常極端的計算方法,與市民大眾的實際生活情況和對住屋的期望有著明顯的差距。
重新定義「住屋需要」 讓公屋與基層真正接軌
說穿了,房委會牢牢掌握著對「住屋需要」的定義,並且將定義設於一個遠超多數基層人士的負擔水平,於是造成只有少數特殊情況的市民,才能符合公屋申請資格。可是,「住屋需要」其實是一個模糊、彈性的說法,房委會的定義及其計算公式也不是不可變改的,問題是我們應當有一個怎樣的標準,以切合更多市民的需要呢?
首先,我們應該徹底轉變入息限額的計算方式,由側重申請人在私人市場同等單位面積的租金水平和家庭開支,改為根據前者的數據並訂立租金與收入佔比的恰當水平,將等於或高於租金與收入佔比的市民通通納入可以申請公屋資源的範圍內。假設我們認定租金與收入佔比應該設於50%,而私人市場同等家庭人數和參考面積的租金水平為6000元,則申請人的收入限額便是12000元了。反之,如果我們視25%的租金與收入佔比才是可負擔水平,在相同租金水平下,申請人的收入限額便是24000元。
建議的入息限額計算方法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好處,一,因為為租金與收入佔比設限,意味著超出上限的市民,就是難以負擔住屋開支的人,因此更加貼近「住屋需要」的定義。二,比起現時刻意加入欠缺彈性的申請人開支水平因素,以淡化對收入的考量的做法,這個建議更加著重重視租金與收入應該如何合理地分配,讓收入因素在收入限額的計算過程中有著更加重要的地位,反映一般基層的生活情況。
其次,在這個基礎之上,便引伸到下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才是合理的租金與收入佔比。根據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及學者研究都顯示,租金應當只佔收入的30%。例如美國的房屋及城市發展局(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在 1981年修訂並沿用至今的建議租金與收入佔比水平就是30%。至於由澳洲學者Matthew Thomas和Alicia Hall的研究亦同樣指出,對於收入水平處於社會最底層的40%人士,其理想的租金與收入佔比應為30%或以下,如果超出這個水平則屬於有「住屋壓力」(Hosuing Stress)的群組,高昂的租金將嚴重影響其生活質素。
雖然30%租金與收入佔比只是一個建議,而不是一項政策或法律, 並不表示每個單位的租金必須維持在租客收入的三成(事實上,美國的平均租金與收入佔比已經超過30%,而澳洲亦有大約四分一的人口平均租金與收入佔比超過30%),但是這個建議的價值,在於它從一個人的收入能力和開支分配提供較人性化和相對合理的租金開支標準,值得作為為基層市民提供可負擔居所的公屋入息限額機制所參考和使用。假如這種標準的話,由於同等面積的一人家庭私人單位平均租金為6,135元,則意味著申請人的入息限額可以放寬至月入20,450元以下的市民。至於二、三、四人的家庭入息限額亦可由現時$19,550、$24,410、$30,950,亦可在分別增加至$27,330、$36,540、$43,010,升幅屆乎39%至50%不等。不但基層勞工都能夠符合有關要求,就連好些夾心階層都能夠受惠,既可以免於承擔私人市場租金帶來的巨大生活壓力,也不必故意放棄晉升或調薪的機會, 為了公屋而過著不合情理的人生。
其實,放寬申請資格還有其他社會好處,例如年輕人盡早覓得穩定的居所,有助作出人生規劃如建立家庭、生育等,增加人口以改善社會老齡化問題;居住公屋的市民人數增加,即是社會對於租住或購買私人單位的需求減少,讓樓價及租金回落;公屋住戶因為租金廉宜而有更多機會消費或儲蓄,提升市民生活質素之餘亦有利刺激經濟等等,實在值得相關部門考慮和採納。
放寬公屋申請資格 解決夾心和更多市民住屋需要
當然,這個建議可能惹來坊間的兩個質疑。第一,就是公屋是為基層而設,如果放寬一人單位的申請資格至月入2萬的市民,即是等於高於月入中位數的市民都有資格申請公屋,豈非有違公屋的原意?然而,在現今的香港,即使收入2萬,都難以稱得上是中產,充其量只是生活條件比基層好一點的夾心,實在不應該完全扼殺他們尋求政府資源援助的機會。再者,在樓價和租金日漸高漲的情況下,大量夾心人士與基層一樣面對著住屋困難的問題,對公營及資助房屋需求殷切,所以就算放寬申請條件讓夾心人士有機會租住公屋也不見得不能體現公帑合理運用的原則。
第二,有市民認為此舉可能會引來大量市民成為公屋申請人,在公屋資源緊絀下,將會拖慢有需要的家庭分配公屋的時間和機會。的確,如果放寬入息限額,將會有更多市民可以申請公屋,不過,只要房委會建立健全的輪候和分配機制,加上政府著力興建更多公屋,並按照各個家庭的實際需要優先讓情況最為緊急的申請人「上樓」,則公屋服務基層市民的原意其實仍然不變。另一方面,市民未能負擔房屋開支,乃是社會問題和成本,足以成為民怨甚至民變的隱患。所以政府的首要考慮,不是有多少人會成為公屋申請人,而是如何增建公營及資助房屋,讓不同收入程度的人士找到適合而可以負擔的居所。因此,不能因為尋求政府基本保障的人有所增加,便無視基層夾心人士的住屋需要,讓他們繼續為房屋問題而大傷腦筋。
房委會一方面容許得到公屋戶籍的人,在家庭勞動成員增加或成員收入上升等情況下,即使入息及資產超過原定的水平,都可以憑藉繳交1.5或2倍租金以繼續享受公屋單位;一方面卻在申請公屋的資格審查中嚴密把關,哪怕入息多出十元八塊都要取消資格,在概念上不可不謂自相矛盾。既然公屋住戶家庭入息增加至超過原本的入息限額,仍然可以被視為「有住屋需要」,那麼,為什麼申請人超出條件苛刻的入息限額,就被視為「沒有住屋需要」?筆者絕非提倡無限放寬申請公屋的入息條件,但是這個條件必須適應社會的現況和市民的能力,因此,是時候讓政府慎重考慮有關意見,真正實現夏寶龍主任「告別劏房、籠屋」的願望。
作者是工聯會社區幹事黃遠康
工聯會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