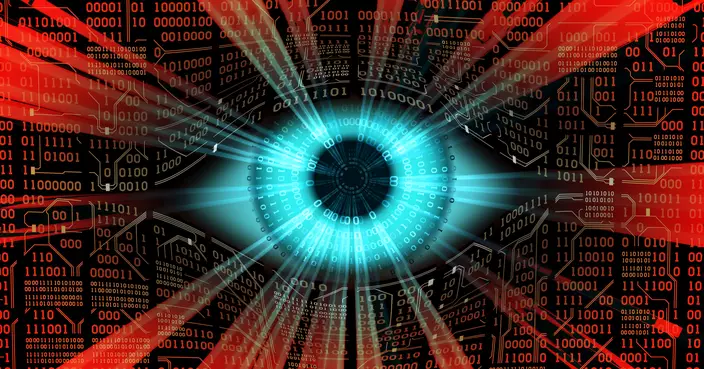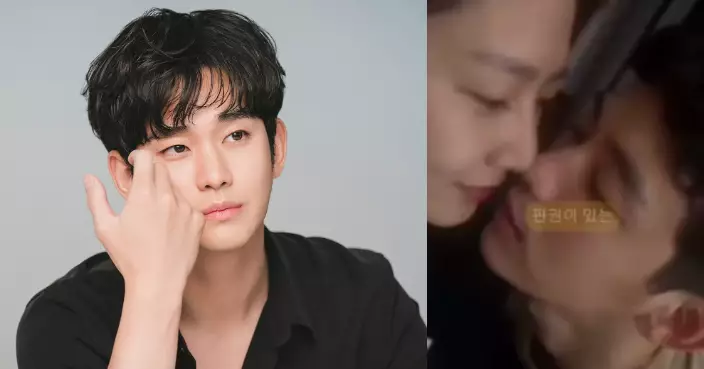我們繼續兩地媒體人的對話,這一集聚焦教育。
2019年,香港爆發令人撕心裂肺的動亂。年輕人、學生以暴力示威,在街頭任意違法,失去血性地用磚頭、尖刀、鐵鎚襲擊不同意見的人、破壞商店地鐵、發動罷課罷工⋯⋯決意「攬炒」香港。一年多來,被警方拘捕的不足18歲的未成年人已近2000人,最小的只有11歲,其中學生佔比高達4成。被捕、坐監、逃亡,許多孩子青春落幕,一生盡毀。
修例風波中,香港滿目瘡痍,學校是重災區。 中學生拉人鏈叫口號、粗口歌響遍校園。中大理大成為「港獨兵工廠」,各內藏數千汽油彈,稚嫩的學生穿上黑衣蒙著面,拉起弓箭,與警方激戰。令人匪夷所思的事陸續被揭發:一些老師在測驗卷、平日的功課和教學時灌輸仇中仇警反政府思想,將歪曲的中國歷史教予學生。1840年英國向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目的竟成了「消滅鴉片」;2020年文憑試歷史科中,試題竟然是「日本於1900至1945年對中國帶來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校長參加遊行,老師在社交媒體張貼謾罵,學生淪為「暴徒」﹍﹍
香港教育出了問題,社會歸咎於此,人們反思於此。
問題真的如此簡單嗎?
前南華早報記者李敏妮和靖海侯有各自的觀點。他們的深度對話,或能釐清此問題,讓真相浮出,開闊並明朗香港的教育前景。
***
第二集:黑暴泛起,教育之罪?
1. 很多人認為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是一面反映香港教育問題的照妖鏡,你認同嗎?這場運動代表了香港教育的完全失敗嗎?
靖海侯:我先談談對修例風波的認識。2019年風波乍起時,香港著名學者雷鼎鳴曾對我說,「這可能是香港1967年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現在看來,雷教授很有判斷力。修例風波當然是一面「照妖鏡」,而且可以說是一面「廣角」甚或「無死角」的照妖鏡。這裡只說主要的三個方面:
1. 從運動形式來看,反映了香港的法治問題。當非法集會天天發生、暴力無日不有,我們很難說香港還有良好的法治文化與精神、社會對法治的尊重和敬畏究竟有幾何。
2. 從運動過程來看,反映了香港的治理問題。從2019年2月份特區政府提出修例,到6月份撤回,再到後面宣佈「THE BILL IS DEAD」,我們沒有看到特區政府應有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決心;同樣,也沒有看到司法機構及時且必要的介入,果斷有力矯正違法行為。
3.從運動參與者來說,反映了香港的教育問題。年輕人躁動、雲集,數千名大中小學生被捕,當然與教育引導有關;2019年,我撰寫的幾十篇包括「人民銳評」在內的評論文章,亦頻繁提及香港教育難辭其咎的問題。
李敏妮:我一向欣賞您的觀察,像是站在一個高處,看清問題,很有新鮮感。2019年的風波,有數以千計甚至萬計的學生參與,很多人簡單地把暴亂歸咎於學校教育的失敗。我與一位教育學者討論過,他說:這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背後包括學校、家庭及社會的因素。深思問題後,我同意他。
舉一個例,大家在新聞都見過一個11歲的小六生王繼祖,據報道,他自小父母離異,由祖母帶大。在黑暴期間,本來反對示威者破壞公物和店舖的他,只看《蘋果日報》被洗腦,言行變得偏激,又認識了攬炒派區議員「天水連線」林進,跟他做所謂地區工作。後來這孩子成立了「天水圍社區關注組」,自封「主席」,每日去「巡區」,他的兩個Facebook專頁充斥著反中、仇警言論。黃媒把他吹捧為明日之星,黃之鋒與他合照,稱讚他為「後繼有人」,令他得到很大滿足感,這也是其他示威青年的寫照。他的中了風行動不便的78歲祖母,眼濕濕地跟記者說很擔心孫兒的將來。那他的問題是教育的錯嗎?據報學校一直很擔心他的安危,但制止不到他。

去年,黃之鋒在Facebook發文,題為【古有15歲反國教 今有11歲落社區】,稱讚王繼祖「投入公共事務」,指「見到年齡比我更加細既同學仔,11歲都已經拋個身出來,心感佩服......」。圖片:黃之鋒facebook
靖海侯:將修例風波顯現的香港問題歸咎於教育問題,是「偷懶」的做法;若完全歸咎於教育問題,則又是不負責任的做法。香港教育有問題是客觀的,是否要承擔主要責任卻是需要質疑的。我們都知道,反對派雖然聲稱修例風波「無大台」,但隨著國安法案件的逐漸明朗,其「大台人物」正陸續浮出,如黎智英之流。這些人走上反中亂港道路,就未必是香港教育所致。而且,香港教育有其科學合理的一面,我自己的小孩有在香港的學校學習,這些學校的老師和課程,有些是比內地更具現代特點的。
李敏妮:一些學者也指出按國際標準,香港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我認為青年的問題跟教育水平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跟學校的學習環境有關。去年7月1日遊行涉嫌用尖刀傷警被捕的24歲黃姓青年,於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任職工程師,與父母居同住慈雲山公屋。已退休的黃父接受記者訪問時透露,港大不時舉辦活動及邀請畢業生參加,其子畢業後仍熱衷參加大學的活動,認為港大累死其子,直言「最衰港大嗰班人」,他雙眼通紅訴說沒錢聘請律師。黃入讀港大時,正值「港獨」思潮滲入校園,那時周永康和馮敬恩等學運領袖在校內搞罷課、在外搞佔中,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被煉成的,那我們又怎可辯稱青年問題跟學校無關?
引起2019年暴亂的原因來自學校、家庭及社會,但當中又互為影響。雖然我們不可以把青年人的問題只歸咎於教育,但學校管理層也責無旁貸。為何大學可以讓校園成為三不管的地帶——港獨和暴力滲入學校、校內藏幾千枚汽油彈(中大8000枚,理大3800枚),學生於校園日夜破壞——而不報警?論到中學,學校平日缺乏教導學生「守法」的重要,亦沒有推行有系統的公民教育(以下會詳細討論)培養學生的品格,年輕人又怎會明白道德的重要?學生在校內拉人鏈、叫口號、唱港獨歌,校長沒有阻止,猶如向學生發出了錯誤的教導,以為學校也接納了這些行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去年,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個七一遊行,再次發生暴力事件,其間一名男子用尖刀刺傷警員。其父其後接受訪問時,說是港大累死其子。圖片:香港01
靖海侯:您的分析很對,「學習環境」異化是香港青年問題的重要致因,也是香港教育問題的主要表現。對於教育在香港問題中的角色,2019年修例風波時,我曾經說過一段話,今天的觀點依然如此,即:孩子是果實,教育是枝葉,社會是主幹,經濟是根莖;而政治體制是氣候,決定陽光雨露。在一個自由、開放的地方,要改良生態環境,必須由表及裏,而不是盯住具體的人群、具體的領域。否則,既治不了表也治不了本,還會引發巨大反作用。
這種認識的邏輯就是,香港問題是「生態病」,教育不過是其中一種惡果。家庭、社會當然要為它負責任。
李敏妮:我喜歡你的用詞,「生態病」。那個病也源於家庭。香港家長普遍認為教孩子只是學校的責任,一有問題,便把責任推給學校。不要忘記家長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地影響著孩子。家長平日有否教導孩子包容,指出違法達義的歪曲性?這個病也源於社會,蘋果日報在2019年暴亂開始的時候, 已經要求公眾資助學生「免費看蘋果」,目的是要灌輸仇中反政府思維給下一代。還有數不盡的假新聞,及洗腦的網上文宣。一個叫「一個人漫畫」的Facebook專頁,在1月8日有一集題為「如果香港獨立左」,內容美化港獨。一個叫「香城教育電視」的卡通視頻,以粉紅色的豬媽媽與孩子的對話,把歪曲思想植入學生的腦中,例如教孩子為何要反抗。看了這些充滿仇恨的資訊的學生,會經過社交媒體把圖像以及思想傳給朋輩,把「病毒」傳開去。

2019年11月28日,理工大學自17日起遭警方圍封第12天後,警方於校內搜出3800枚汽油彈。圖片:香港01
2. 有人批評學生心智未成熟,不應被鼓勵參加社會運動。中國近代的革命不都是由學生帶動的嗎?今天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一定是錯的,一定代表教育出了問題嗎?
靖海侯:學生參與社會運動、推動社會革新,可以有多種方式,但每種方式只要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場景下,才能定義其正當性。我們不展開分析,只說修例風波前的香港:第一,「一國兩制」是否得到全面貫徹落實,香港特區是不是實現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司法獨立?香港市民是否享有相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充分的自由和權利?特區政府是否足夠謙卑和清廉?第三,相互移交逃犯是否是司法所需,是否有國際慣例可循?所以,在香港發展的這一階段,我們看不到通過激烈的社會運動實現變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修例風波一定是蓄意的,且一定不是以反修例成功為最終目的的。其正當性和積極性,就無從談起了。
因為參與修例風波的以年輕人和學生為主,人們自然要問責香港的教育。
李敏妮:您的分析很有透析力,而你的語氣很特別,有一種超然的威嚴,在香港媒體很少見到。說到革命,我覺得很可笑,香港是民不聊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嗎?政府是否黑衣人口中的「暴政」和「高牆」?回歸以來,政府事事忍讓怕事,只能是「雞蛋」,又怎會是高牆呢?這些學生又怎能與五四運動的發起人陳獨秀等人相比,後者為了改善社會,而這些拿著鐵鎚的「細路」只是誤信看似偉大的口號,以為當了革命家而已!
我的學者朋友跟我說,為了迎合世界新經濟的需要,由2000年開始,教育局在中學進行課程改革,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不同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我想,如學生已被培養出「批判性思考」,根本不會明知犯法也以暴力抗爭。但他指出亦有人能反駁我的說法是錯的,指年青人出來抗爭也可以反映他們有批判性思考 ——認為應該走出來對抗極權。
靖海侯:內地法學教授羅翔有句話,「法律是對一個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都已經違法了,所謂「批判性思考」即毫無存在價值。社會鼓勵「批評性思考」,只是「思考」,並不是讓學生們起來暴動的。以暴力運動的方式證明自己有批判性思維,可以說是腦殘行為了;而如果以此認為這些人證明瞭批判性思考能力建設的成果,更可以說是愚蠢透頂了。
「批判性思考」是必要的,這是社會不斷迭代發展的思想根基。但人們需要明白,此「批判」著眼於「建設」,體現於推動社會的討論,且不是無邊無際的,枉顧法律和歷史的。

年青人出來鬧事是否反映他們有批判性思考? 靖海侯說:「內地法學教授羅翔有句話,「法律是對一個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都已經違法了,所謂「批判性思考」即毫無存在價值。」 圖片:網上
3. 主流觀點認為,2019年的暴亂是學校充斥了黃老師黃校長荼毒仇中反政府思想給學生所致,您的觀點怎樣?這些老師又是誰影響了他們?傳媒和教協又有否責任?最近自由黨議員張宇人倡在教室裝閉路電視,您同意嗎?
靖海侯:修例風波中,香港一些老師有匪夷所思的言行。還記得一名老師在社交媒體發帖,公言「黑警死全家」。而當時有的學校,學生因參與黑暴被逮捕,一些校長只是包庇、不是譴責,只有縱容、沒有規導,甚至還阻止警方進入校園搜查。且不說學生之前受到的是什麼教育,單單這些事情就會讓學生產生誤判和迷思,模糊了對是與非、善與惡、黑與白的認識。所以說,學生走上違法犯罪道路,這些老師和校長是「有罪」的。
李敏妮:模糊了善與惡成為了問題的根源。2019年,市民揭發一個又一個老師,在授課和工作紙中,把「暴力示威者是善良、執法的警察是邪惡」等是非不分的意識,灌輸給學生。有人會認為,這些老師只佔全港共7萬多名中小學及幼稚園老師一個很小的百分比,影響有限。
先看看數字。截至去年10月,教育局共接獲262宗教師在社會事件中涉嫌專業失當的投訴,226宗已完成調查,當中85宗不成立,即141個案成立。同時,截至去年6月,至少有110名大中小學教職員因參與黑暴活動被捕。假設一個老師每星期教4班學生,每班30人,每個老師便影響了120名學生;如有200名老師灌輸壞思想給學生,他們共影響了24,000學生,他們再經過朋輩把歪曲思想傳開去,受荼毒的學生人數便不敢想像。
靖海侯:當然,老師和校長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是「真黃」,本身可能就是參與暴亂的一員;有的則是「怯黃」,畏懼於黑衣人的「黑色恐怖」和社會上所謂的「主流民意」,出於自保或不惹麻煩的動機不得不遷就、不能不表示「鼓勵」,即我們常說的「黑色恐怖」。比如修例風波時,嶺南大學校長被「挾持」去參加遊行,未必代表了他本人的真實意願。

靖海侯說,在修例風波中,學生因參與黑暴被逮捕,一些校長只是包庇、不是譴責。「不說學生之前受到的是什麼教育,單單這些事情就會讓學生產生誤判和迷思,模糊了對是與非、善與惡、黑與白的認識。」圖為中五男生曾志健於2019年10月1日向警員襲擊,防暴警為保命開槍自衛。但其就讀的中學校董會被指沒有半點譴責其瘋狂襲警的學生曾志健,反而指控警察因為自衛開槍是「違規暴力」圖片:網上視頻截圖
李敏妮:我們也要探究大學老師的情況。由於沒有研究,我不敢確定大學學者政治偏頗的情況,但有一次到一個港大法律學系的講座,情況真的嚇我一跳!事緣一位港大法律系教授邀請我到一個關於「公民動盪」 (Civil Unrest in Hong Kong) 的講座。當時是去年1月,香港給黑暴打得支離破碎,我還以為是一班學者討論,在暴亂後社會怎樣可以復原。怎知席上的六位講者(除了一位南華早報舊同事)大都以歪理支持抗爭,他們大部分是教授級,來自中文大學、科技大學、香港大學,有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有研究政治的,有科大社會科學部的chair professor。他們以powerpoint宣示他們的研究,但大都以偏門的學術理論(戴耀廷常常用這招)支持其政治主張,令我在座位上震驚亦憤怒。其中一個大約30來歲的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女教授,訴說監禁佔中人士是何等的不公義,另一位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女教授,則批評中聯辦對香港乾預。
講座完成,我是最後一個人舉手發問。一開始,我聲音有點顫抖,拿起咪用英語說「在這裡,我是一個小眾(I am a minority here),我有點害怕發言,但為了公義,我決定發聲」,全部講者聚精會神屏息地望著我,很多觀眾回頭看我。我繼續:「剛才那位學者批評中聯辦乾預香港事務,其他學者也說著中國怎樣乾預香港,我想指出香港的法律原則是「一國兩制」,但你們的評論只強調「兩國」,那「一國」在哪裏?」(You have focused on 『two systems』, where is the 『one country』?) ,即時學者們的表情非常尷尬,沒有人回應,我再繼續:「一國兩制是在基本法中訂明的,若然只著重兩制,而沒有一國,這是違反了基本法。(This is breaking the Basic Law) 」我聽到背後有一兩下笑聲,不知是恥笑我還是恥笑講者,前面有幾位觀眾回頭以欣賞的目光望著我,無論支持或反對,我也不怕!只想說出事實。後來那些學者回應時都面目無光支吾以對,無一能有力反駁!身為學者理應持平,但他們卻把政治立場凌駕於學術中立之上,利用研究把歪曲思想傳開去,教出來的學生會怎樣 ?他們亦有機會成為將來的學者,朽壞了的思想就這樣在教育裡腐化壯大。
「香港教師協會」也是一個黑暗力量。如同政治團體的教協公開支持學生參與反修例運動,影響了老師對這社運的看法。代表教協的一向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包括每年舉辦六四晚會的已故司徒華,和現在學者出生的葉建源,很有影響力。教協也一直幫助老師解決與學校的紛爭,如同教師工會。他們支持什麼,怎會不影響老師的取態?
靖海侯:您的提問很有力量,我之前也曾質問過經濟學人,講明他們的偏見。對於教協與學校的關係,其實更像教育與社會、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於此方面,有個觀點是「社會結構決定了教育制度」,但教育很難去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我們既然說香港問題是「生態病」,那也可以說教育本身也是香港問題的受害者,繼而又在社會問題的荼毒下成為問題的一種。

港大法律系去年1月21日舉行的 Civil Unrest in Hong Kong講座。圖片:港大
李敏妮:您說「教育本身也是香港問題的受害者,繼而又在社會問題的荼毒下成為問題的一種」很有深度,把這個糾纏不清的關係釐清了。我認識一個研究公民教育的學者,他希望社會不要把「一小撮老師」的問題無限擴大,就如對方放大警方在示威期間的錯失,否則只會鼓勵不同派別繼續互相攻擊,增加仇恨,影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穩定發展,「這不是公民教育」他說。他的說話衝擊著我的思考,我認為傳媒在譴責問題的時候,亦要尋求解決辦法,只是「鬧鬧鬧」,香港又怎能和解,社會怎會康復過來?
這位學者朋友嘆息暴亂後,有些社會人士意圖在每一個生活環節「肅清」所有問題,包括有人倡議成立量刑委員會,是對不同專業的入侵,但他說「如我要抗逆這種大眾的想法是很危險的。」我欣賞他的思考超越人群,不隨波逐流。社會缺乏互信已到一個病態的程度,我反對在教室裝閉路電視,人一定會犯錯,有的時候說錯話,若果錄影會被人拿來作證據控告,老師怎能輕鬆施教?就等於我做記者,問問題都會有出錯,若有人錄影訪問過程,以後我就不敢問敏感的問題了。雖然我們應該有機制去監管失德,但有心騙人一定會走法律罅,最後其實要看人的自律。這需要整個社會的反思、改變,才能做到。
靖海侯:我的理解是,您的這位朋友不是反對「撥亂反正」,而是反對「矯枉過正」,反對非常手段的常態化,反對亂世重典在運用於正常階段。這是一種理想化的認識。
對於要不要在教室里裝閉路電視,我認為這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方法論問題。解決香港問題,需要有步驟性安排,第一步是去除亂象,第二步是鏟除亂象滋生的土壤。裝閉路電視,在去除表面的亂象上是有效的,但對於第二步的作用很有限。
李敏妮:我喜歡您的看法,有策略和彈性,這是從政者應有的智慧,可惜我們只是記者!
4. 2019年11月3日,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在參與示威期間於將軍澳墮樓停車場墜樓,腦部重創命危,隨後校長史維為事件與學生舉行公開對話時,有本地學生公然在校長面前毆打一名曾經發言的內地生,之後引發在香港的大學就讀的內地學生逃亡。你看到他們逃離香港的那一幕,你有什麼感受?那一幕反映了什麼?
李敏妮:當天在網絡上見到那名發言後的內地生離開座位時,一名黑衣蒙面青年阻著去路,並疑似假扮被他推跌。那學生一路從禮堂走出來,一路被那些香港學生追打,被打數拳額頭流血,眼鏡也被打掉,很快有人開雨傘預備「遮蔽」打人的人。若不是保安立即上前保護那名學生離去,他必被打至重傷昏迷。當天香港01的標題竟然寫上「一學生推跌他人後被打」,視頻中更稱「一名內地生撞跌一名本地學生,雙方隨即發生衝突。」是雙方衝突嗎?根本是有人被打!這就是明目張膽的偏頗了。當晚傳出學校立即安排旅遊巴接載內地生返回大陸,隨即城市大學、中文大學的內地生也在逃。中大內地生在馬料水碼頭排隊上船,亦有錄音傳出,當晚有的士司機「漏夜」接載從中大逃出來的內地生過關。逃亡的大陸學生如置身驚慄片中。
靖海侯:這件事我比較瞭解。當時,科大的一名工作人員還曾聯繫我,希望我為內地學生提供一些幫助。無疑,這是科大的恥辱,對科大精神傳統的背棄。我們都知道,科大素有愛國愛港情懷,當初成立的一個目標即是為國家培養科技人才。但科大在修例風波中出現了這樣的事情,說明瞭什麼呢?1.當香港「泛政治化」,大學校園不可能成為「世外桃源」,也會被感染;2.當香港社會失序,教育秩序也會受到衝擊和挑戰;3.當香港的大學生與反中亂港勢力同流合污,學校里已不可能「擺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李敏妮:原來您有份幫他們逃亡,您當時是否感到心驚動魄?
靖海侯:我當時有兩個感覺:1.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2.止暴制亂的形勢已經非常急迫了。
李敏妮:這件打人事件讓我看到兩個青年人的現象:1.記得校長喝止那些打人的學生,但沒有人理會,公然犯法;2. 學生對內地人的仇恨超乎常理。要解釋第一點,大家回帶看看戴耀廷自2014年佔中前,已開始用「違法達義」概念洗腦年青人,在2019年反修例事件前後,再「落藥」。示威爆發,為了「公義」,學生便公然違法;示威成為一個大染缸,在此暴力被「正常化」,如病毒般快速在年青群體中互相感染。對大陸人的仇恨又從何而來?相信跟父母平日潛移默化身教「看不起大陸人」(當中的原因,我們會在「兩地關係」的一集詳談)、還有傳媒的荼毒、和朋輩的影響。
靖海侯:這方面,我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本地生毆打內地生,並不能說明兩地學生有衝突關係;恰恰相反,打人者是想借此塑造這種衝突關係,這是黑衣人實踐反中亂港勢力的「陰謀論」。特別是內地同胞,不應該從這一事件中認為科大或者香港不歡迎內地生;否則,就中了他們的圈套,讓「親者痛仇者快」了。
5. 近年,學生會當道,民主牆是他們攻擊中國和政府的戰場嗎?當中的文宣是否成為洗腦大學生的來源?應否肅清大學內任何反對的聲音?
靖海侯:香港幾所高校的所謂「民主牆」我都去看過,概括起來,有幾個特點:1.文宣材料隨意,跟巴士站牌上的小廣告差不多,質素很低,更談不上fact check的內容;2.關注者寥寥,每次我去看的時候基本上都看不到有人駐足,看的人大多都是來學校參觀的人,且抱有一種「獵奇」、「好玩」的心理;3.沒有管理,「民主牆」成了學生會的「自留地」甚至是「獨立王國」。可以說,他們的這種所謂「戰場」其實影響力很低。我們所以關注到它們,更多還是傳媒放大的結果。
李敏妮:您很用心瞭解香港的問題,連大學的民主牆你也去觀察,您的評論很持平。大學應該提供一個「開明」環境,讓學生在未到外面世界實踐理想之前,有一個可以思考事情的地方,我們不用清除民主牆。在大學的過程中,學生可以接觸不同的言論,才能學懂思考,辨別好壞,思想被衝擊及擴張,我相信這才是教育。話雖如此,底線是校內的言論和活動一定要合法。
靖海侯:對!是否阻止學生會在「民主牆」上的行為,首先考慮的不應是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依法辦事的問題。從大的方面講,可以對照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本地有關法律;從小的方面講,可以檢視學校的有關管理制度。我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在香港的任何一寸土地上,都不存在「法外之地」。於此,「民主牆」不是例外,不應當成為例外。

香港多所高校的民主牆不少都曾出現「港獨」標語,學生會指,校方曾承諾不乾預有關民主牆的管理。 靖海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在香港的任何一寸土地上,都不存在「法外之地」。於此,「民主牆」不是例外,不應當成為例外。」圖片:網上
6. 去年8月,中大學生會寫給新生的家書自命學校為「暴大」,鼓勵新生延續「暴大人」的反抗精神。11月20日,過百學生趁中文大學畢業禮,在校園內戴面具遊行,高叫港獨口號和標語,國安處其後拘捕拘8人。學生會不滿校方報警,和校內保安人員協助警方調查,於是在大學發動不合作運動,包括進校時不出示學生證,引致學生與保安員衝突,有學生向保安員撥白色粉末,亦有學生以粗言穢語辱罵及欺凌要求出示學生證的保安員。事件反映了什麼?《港區國安法》已經立了,社會不是應該已經平靜了嗎,為何仍有這些蠢蠢欲動的學生?
李敏妮:我看過那些中大生與保安衝突的視頻。在其中一個,見到一個斯斯文文戴眼鏡的中大生罵保安員「四腳狗舔林鄭」、「你個仔都入唔到來讀(中大)啦」。在另一個視頻,學生用極難聽的粗口侮辱要求他們出示學生證的保安員,多次稱他為「退休狗」、恥笑他「毅進仔冇書讀」,這個保安員EQ好高,沒有反罵他們。這些學生滿口道德,例如對保安員說「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學術自由?」、「大學是一個開放的地方」;但同時他們的行為卻非常不道德。拍片的人自稱是新亞學生會幹事,除了一直用粗口大罵保安外,還拍下保安員編號,呼籲看片的中大生把這名保安員「起底」,這就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不守道德,嚴人寬己的雙重標準,不就是反修例示威者的寫照嗎?
國安法雖然立了,但試想想,200萬人遊行的真正數目,當時路透社報道裡估計有50至80萬,當中一定有很多學生,他們能夠一下子明白過來嗎?國安法止了血,傷口還在裏面痛,法例只是讓社會的反動勢力壓下來,這些年青人只成為了「暗流」、「地下人」。國安法改變不到他們,更可能令他們心中怒火更盛,等待時機一觸即發,只有社會、學校及家庭的正面教育才能改變他們。作為傳媒,我們的工作現在才開始,必須把年青人的扭曲的思想逆轉過來,任重道遠。
靖海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的問題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會因為國安法就瞬間消失。我曾經說過,國安法不是萬能的,也不能指望國安法解決香港的所有問題。中大這些國安法後的亂象,說明的還是香港社會政治基礎不牢的問題。這些參與鬧事的學生一方面是因為無知無畏,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試探。最近警方已經拘捕了其中一些人,通過這些執法行動,他們將開始學會敬畏,認清底線。但要把他們頭腦中的思想扳過來,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方面,就需要教育發揮作用了。
李敏妮:對,現階段最重要是令他們生出「敬畏」,知道他們的行為不是沒有後果的,便會大大收斂!

去年11月20日,約百名中大學生趁畢業禮戴面具,在校園遊行集會,期間高叫「港獨」口號及標語。圖片:Getty Images
7. 很多人批評香港的大學校長們對待反修例運動學生軟弱無能,縱容學生,導致大學成為「港獨兵工廠」(警方在2019年11月的中大戰役後校園內檢獲超過3900枚汽油彈)。但日前剛卸任浸會大學校長的錢大康接受訪問時,批評社會將整個年青人的問題推卸給教育界,是「非常不負責任」,說這是「社會問題,不是教育問題。」 同時,近日有呼聲要求罷免段崇智校長,您認為我們應該革大學校長的命嗎?大學管理層在處理今次社會事件中犯了什麼錯?應如何改變?
靖海侯:早在2018年1月,我就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香港高校管理層的腰桿可以再硬些》,當時香港媒體普遍有轉載報道。我在文章中說,「象牙塔內,醜聞不斷,讓人寒心。究其原因,無非兩個方面:一是學生犯錯,二是校方失責」。香港高校管理失之於寬、軟的問題是「老毛病」了。
至於錢大康的話要一分為二看待。從宏觀上講,他的話是對的,教育問題肯定不是孤立的;就某一學校作具體分析,比如中大,錢的話又有「卸膊」之嫌。
李敏妮:同意,我是認同錢大康的觀點的,青少年的問題怎會只是教育的錯?但我亦要持平地指出,大學管理層必須負上很大責任。遺憾的是,事件過了多月,仍未見大學從錯誤中學習。在2019年破壞校園、打同學、辱罵校長的大學生成千上百,有多少已被懲處?中大副校長吳樹培在立法會說對於行使暴力等違規學生已按既定程序懲處,人數是10人以下,並沒有透露什麼懲處。

2019年11月13日,中大一夜與警方對抗後的清晨,大批學生暴徒徹夜守校至天明。圖片:美聯社
老師聽到要懲罰學生會很心痛,讓我說一個人故事,大家就會明白懲處並非殘忍。在中五的時候,當時我15歲,因為貪心和貪靚,常常跟一個同學到商店「高買」,偷自己想要的東西,例如化妝品、絲襪、漂亮的衣服等。上得山多終遇虎,有一次在百佳超級市場給職員抓住了,我很害怕,求他們放過我,但職員心硬,最後被帶到旺角警署。爸爸趕來見到我,我以為他會打罵我,但他沒有,只顯得很擔心,我很難過令爸爸失望,現在回想也哭了出來。後來警方給我機會,爸爸帶著我站在旺角警署的警司面前,接受警司警誡,那房間的凝重氣氛仍然歷歷在目。這件事令我非常羞愧,驚嚇,從此我要求自己非常誠實,決心要行一條正路。當初如百佳的職員出於「仁慈」沒有報警,放我走,我今天會變成什麼?如警察沒有給我機會改過自身,留有案底,我還有前途嗎?還能從香港大學傳媒系碩士畢業嗎?回想,整件事的重點是「愛」。大學校長懲罰學生不是無情,而是出於愛。如果一個人做錯沒有後果,又怎會反省?若真心改過,社會也應該考慮給他們機會,重新來過,生命有take 2。
靖海侯:您還挺勇敢的,香港欠缺的就是這種整體反思的力量。保護、愛護學生是學校的職責,但姑息、包庇不法無德的學生和老師,危害更甚。修例風波這麼多學生被捕,這麼多學校被砸,已經說明瞭姑息、縱容問題的嚴重性。香港高校管理層需要認識到:嚴管也是厚愛,有心更要有力,要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惟其如此,校園才有秩序,風氣才能淨化,學校才不會成為「暴徒訓練營」,砸了學校招牌,毀了學校名聲。
李敏妮:同意,包庇學生,危害更甚!中學校長見到學生在校園拉人鏈、叫口號唱港獨歌,為何不阻止他們?中大生在校內練武功,練習掟汽油彈,預備以暴力對抗警方,大學有否召見學生調查?有否報警?如當初中大學及時阻止,相信不會有那麼多年青人以身試法。
靖海侯:是的。比如段崇智,當時罵他「段狗」的首先是黃絲,等他「跪低」了又成了「段爸」。我們可以想一想,段本人是想被人稱他「段狗」呢還是「段爸」呢?我想他都不願意。要避免這種情況,就得有是其是非其非的勇氣,嚴守學校就是學校的定位,不跟著社會一時的思潮和輿論走。比如科大校長史維,修例風波時也被圍堵了很長時間,但堅持了立場,結果就不會像段崇智那麼壞。

靖海侯說:「比如段崇智,當時罵他「段狗」的首先是黃絲,等他「跪低」了又成了「段爸」。我們可以想一想,段本人是想被人稱他「段狗」呢還是「段爸」呢?我想他都不願意。」圖為中大校長段崇智於2019年10月10日,與學生及校友進行近4小時會面後,得到學生舉手支持。圖片:明報
李敏妮:你點出了一個香港的核心問題,令我一言驚醒。政府帶頭怕輿論,其他人都一起害怕,於是被社會輿論牽著走!我們亦要體諒這些教育者,他們從沒有經驗處理顏色革命,整個香港也未有遇過,真的如置身驚濤駭浪!就如世界各地的領導人沒有經驗處理新冠疫情一樣,都是一邊做一邊學,經一事長一智。校長門的怯懦也與黑衣人太兇猛有關。2019年若有中學反對學生的行為,就會招致黑衣人「接放學」,向學校掟雞蛋和雜物。大學校長都是住在校園裏,可以有警察24小時保護他們的家人嗎?我有一個舊上司,在大學裏被這些黑暴學生包圍用粗口辱罵奚落,最後被迫到警察局擔保一個被捕的學生記者,看到有關視頻我非常心痛,他的表情告訴我他對學生非常失望。
如果我是大學的管理層,我不會在這些人面前退縮!絕對不會!我會每次報警!如果為人師表也懼怕黑勢力,不但縱容年青人犯法,還會令年輕人和社會人士學會「自保避事」,不敢以勇氣面對問題,也不明白伸張正義的重要。
靖海侯:對這些校長不能求全責備,也不能據此認為他們是無辜的。正如修例風波所暴露的香港問題,在處理修例風波上的表現也暴露了香港高校管理層的勝任力問題。一個好的教授未必是好的校長,我相信段崇智在學術上有造詣,但他在處理中大的修例風波上,可以說是一錯再錯了。我們可以不懷疑他處理問題的初心,但確實已對他繼續擔任校長一職不再抱有信心了。特區政府應該考慮這方面的人事調整,段崇智自己也應該考慮辭職。這不是針對段崇智個人,是著眼中大的健康有序發展。
8. 香港政府在回歸後推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簡稱教改,包括在2009於中學推行3+3+4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的教育制度。新學制其中一個焦點是加入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成為高中課程的必修科,鼓勵學生討論社會議題。科目的六個教學範圍,包括「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給予老師自由選擇香港和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議題,讓學生討論和做功課。
很多人歸咎通識科是荼毒學生仇中反政府的根源,終致2019年的動亂,應否如外間所說,取消通識科?世界各地應該都有通識科,是制度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怎樣可以防止教師灌輸錯誤思想給學生,防止校園政治化呢?
靖海侯:在看待香港問題時,人們容易歸咎於教育;在看待教育問題時,人們容易歸咎於通識科。這都有片面性。在我看來,通識科的問題不在於通識科本身,而在於教通識科的人。我曾經專門去上過幾堂通識教育科,對教什麼、怎麼教,任課老師有很大的自主權,教授同樣的教科書,完全可以給出完全不同的觀點。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
李敏妮:你真的很會求真,這是記者應有的態度。我跟一個中五學生談論過,他有修讀通識科。他說,通識科需要學生討論香港和中國的社會議題,但老師有很大自由度選材怎樣教授,例如他們可以討論香港的立法會選舉、不同黨派的分佈、中國的憲法修改等。由於這種自由度,老師可隨意選擇一些對政府及中國負面的題目,把自己的政治取態灌輸給學生,同時不選擇討論任何正面的社會發展,這便很容易令學生得出結論,認為中國不好。每一個國家都有缺失,怎能只看負面的新聞,而作出評價呢?
靖海侯:現在特區政府已經開始對通識科的整頓,要求教科書送審。這是必要的一步,但解決通識科問題的關鍵,還是整肅通識教育隊伍。之前被媒體曝光的一些相關教育醜聞,都是學生家長揭發的。我想問的是,校方之前知不知道?毫無疑問,校方肯定知道。知道而不去矯正,所以教師的考評制度和學生的考試制度有問題。從考評和考試制度入手,才能抓住問題的關鍵,才能避免通識科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通識就是一種知識,不應該附加太多主觀的內容。
李敏妮:完全同意,問題在於教師。一個研究教學法的學者跟我說,通識科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負責的老師會否濫用職權灌輸自己的政治立場給學生?就等於傳媒的報道以及學者的研究,若果寫作的人有心扭曲結果,一定做到的,難道要取消傳媒及研究的專業?重點是老師會否用持平的態度讓學生學習。根據我蒐集到的資料,現時老師的認證及持續培訓,都沒有教導「老師不可灌輸政治立場給學生」的概念。我們可以從培訓入手,讓老師明白教導學生應該持平。

2009年,通識科成為高中必修科目。李敏妮認為,通識科問題的重點,在於老師會否用持平的態度讓學生學習。 圖片:BBC
9. 現時中國歷史只在小學的常識科教授;中學的初中(中一至中三)沒有中國歷史教育,高中(中四至中六)的中國歷史科是選修科。很多人認為香港年青人的仇中恐中情緒,是由於學校沒有教導學生中國歷史,你同意嗎?香港應否把中國歷史成為中小學強制性的科目?為何?
李敏妮:香港人普遍的仇中情緒是跟他們不瞭解中國歷史有關,這是由於在教育制度裡教導中國歷史不足。說來慚愧,我在80年代,讀中四中五的時候,是選修歷史的,但課本的內容,大部分是要學生「死記」歷史事件、朝代年份等,完全提不到我對歷史的興趣,讀歷史好像是為了考試,這樣我就白白過了兩年。多年來,我對中國過去發生的事是一片空白的,那麼沒有讀過歷史的人,可以想像他們是如何不瞭解中國了。如對歷史有基本的認識,香港青年便不會那麼容易相信傳媒的洗腦。教育局應該把歷史定為必修科,盡快在中小學教授。
靖海侯:強制是為了培養習慣。重點是要讓學生們喜歡歷史知識,並真正能從歷史知識中感受到國家和民族的驕傲。香港學校沒有不教授國家歷史的,客觀上已經普遍存在了。解決國家歷史教育的問題,關鍵在於教什麼、怎麼教。其中:教什麼應當是全面的、合比例的。比如:既然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教育就應當以國家歷史為主、世界歷史為輔;講授中國近代史,就不能只講1976年以前、不講改革開放以後;講授西方國家殖民史,就得聚焦於殖民,而不是吹捧什麼「西學東漸」。怎麼教方面,就是歷史課教師隊伍建設問題,必須把准他們的歷史觀,不能讓有私心、夾私貨的人混進來,誤導孩子們。
李敏妮:對,歷史課程內容也要改革,必須教授近代史,香港青年便會明白列強一直是怎樣欺凌中國、便會看穿他們今天的把戲;明白日本如何殘暴的侵略中國,明白是弊多於利,便不會被試題洗腦。
靖海侯:這方面,我問過不少「黃絲」乃至「港獨」分子,問他們是否瞭解國家歷史。他們都回答「非常瞭解」,甚至表示比內地人更瞭解。於此方面,我們可以再探討兩個問題:1.他們有歷史知識,是否有正確的歷史觀?2.他們學到了歷史知識,是否還被灌輸了紛雜的歷史觀點?從他們的「仇中恐中」的現實表現看,我們可以就此反思。
「歷史是嚴峻的」,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正如上面通識科的問題,如果可以任意解構、隨意闡釋、按照主觀好惡進行褒貶,或者根據個人所需選擇揚抑,這樣被教出來的歷史還有權威性、嚴肅性和準確性可言嗎?!所以我認為,香港年輕人對國家和歷史認識不足、不當的問題,首先還是教師的問題。

去年5月14日舉行的DSE歷史科考試,出現被指「無視日本侵華暴行」的試題,涉嫌洗腦。題目引述兩段資料 C 和 D,然後要求考生評論「1900年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是否同意此說?圖片:網上
10. 很多人批評香港的教育是以考試為中心(examination oriented),令老師和學生注重學業成績、操練應付考試、學校缺乏時間栽培學生的品德、思考和分析能力,引致年青人容易被誤導,上街參與非法示威。這種以考試為中心的教育模式真的有問題嗎?若是,我們應該怎樣改變?
靖海侯:應試教育問題不單香港有,內地一樣,其實國外也差不多。把青年問題歸咎於考試問題,也是片面的。我們要問的是,通過學習,年輕人是否可以實現成長髮展,是否能夠打破階層板結、實現「上流」。如果不能,那這種考試就是與社會脫節的,不能為個人和社會帶來福祉的,就必須改革。
李敏妮:80年代末期,香港工廠北移,本地漸漸走向「知識型經濟」,社會向上流的難度更高,人們必須讀書才可找到機會。因此過去20多年,年青人是這樣長大的:無論學校或是家長也告訴他,你什麼也不用理,不用做,只要讀到書、入到大學就是「叻仔」。上學不是為了學習,而是考試,花人生寶貴的20多年在此。我不知道自己這樣想,是否太離地。
為了考得好成績,年青人變得功利,大多自我中心,要求別人處處遷就自己,一遇到不合心意的事,便感到被不公平對待、像世界末日,必須大吵大鬧爭取。學生每天忙於操練,沒有空間思考事情,判斷對錯,學校及家庭亦缺乏時間栽培學生的品格和分析能力,於是學生容易被人誤導。修例風波中無數青年上街,正正反映香港年輕人是如何的脆弱!
靖海侯:學生的天職就是學習,考試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也有助於培養他們的競爭力和抗壓力,總體上問題不大。問題在於學生們常被社會不良思潮誤導,覺得學習沒有用,或者認為「學到的東西」在鼓勵他們不要專注於學習。比如社會上所謂的「違法達義」之說,就是慫恿孩子放下課本去非法「佔中」、去參與反修例,我們能說這是考試的問題嗎?還是那句話,學校就是學校,學生就是學生,社會應當支持學生坐下來讀書而不是站起來運動。這才是根本。
李敏妮:學校和家庭缺乏教導孩子「守法」,也是問題的根源。

很多人批評香港的教育是以考試為中心,學校缺乏時間栽培學生的品德、思考和分析能力,引致年青人容易被誤導,上街參與非法示威。靖海侯說:「社會上所謂的「違法達義」之說,就是慫恿孩子放下課本去非法「佔中」、去參與反修例,我們能說這是考試的問題嗎?」圖片:美聯社
11. 2012年香港的反國教(反對國民教育)示威遊行,要求政府撤回具爭議性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反映了什麼?對後來的社運以及香港教育帶來了什麼影響?很多人批評當年的特首梁振英最後跪低撤回科目是導致今天的亂局,你同意嗎?他有選擇嗎?
靖海侯:類似運動不過是香港反對派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只不過是他們在教育這個領域上開闢的新陣地,反映的並非學生的問題,還是香港反中亂港勢力興風作浪的問題。但這個運動的危害更大,它讓很多學生有了錯覺,開始否定自己所接受的教育,進而開始否定整個社會。更要命的是,因為特區政府最後的「跪低」,還讓他們嘗到了「勝利」的滋味,進而激勵參與者更為激進,更多的人參與社會運動。這,正是反中亂港勢力想要的,他們就是要把整個香港社會裹挾進來,包括孩子。
李敏妮:你說得很好,就是給這些孩子和這些「香港人」嚐過了勝利的滋味,以為只要自己站出來就可以改變世界,這種心態毒害最大。事件對香港社會帶來極破壞性的影響,培養了以黃之鋒為首的反對派學生,正式為學生參與政治打開了大門,為佔中和反修例運動提供了大量「精兵」,終令暴力示威一發不可收拾。如果當時梁特首沒有妥協,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可能不會發生。CY現在振振有詞,狠批參與黑暴的年輕人,指控教育的缺失,他忘了自己當初撤回科目嗎?之後提都沒有再提推行國教了。他應否為此負上一點責任,值得大家反思。
靖海侯:特區政府此前在社會運動上的處理手法,我們可以回望香港回歸後的這23年,幾乎可以說,反對派全部取得了「勝利」。特區政府當然可以說是社會環境和民意使然,不得已而為之。但我們要問:1.真的需要事事妥協嗎?2.妥協後真的帶來社會和諧了嗎?3.如果強硬一點,結果一定就那麼壞嗎?
李敏妮:這一直令我質疑,形勢真的這麼危急須撤回科目嗎?「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內容涵蓋公民教育,對培育年青人非常重要,就是因為反對派的妖魔化,死掉了!國教事件後,教育局只用指引形式,要求學校提供「德育及公民教育」給學生,但學校如何做和做多少時數,沒有規定。學校提供的都是「片段化」的公民教育,例如把早會校長的話,或是老師上台分享,當公民教育,向教育局交「功課」。我曾幫一位香港教育大學的美國學者,編輯他的英文小冊子,指導學校如何推行國民教育,辛辛苦苦做好的文件派發給中學了,有何用?
靖海侯:很多人批評「五十年不管」的問題。但大家也可以看看:取締香港民族黨,用的是特區法律;懲治非法「佔中」發起人,用的也是特區法律;修例風波中被捕的人士,也都是因為觸犯了特區法律;近期教育局為一些黃絲教師「釘牌」,也是適用的特區法律。所以在國安法出台前,特區政府不是沒有辦法應對社會問題,而是過於保守、過於遷就,或者說過於怯弱,他們沒有承擔起應有的管治責任來。
李敏妮:政府是時候拿出勇氣,轉弱為強。教育局應盡快在學校推行有系統的公民教育,就算不是獨立成科,也要有指定時數。公民教育應該教導《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讓學生明白聯合聲明不是英國所聲稱的條約,而是大家的statements、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的管轄權。公民教育也可以教導民主和人權的好處和應有的界限、公民責任、個人如何貢獻社會、什麼是愛和包容?公民教育也應該教導國民教育,讓學生重建中國人的身份,重新發現自己是中國人,不會忘記他們的根。

香港傳媒形容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是香港社運發展的重要分水嶺。李敏妮認為,當時特區政府選擇了妥協,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圖片:香港01
12. 大家看到2019年上街的並非全部都是中學生、 年輕人,還包括很多中年,甚至老年人,他們明顯沒有接受通識科教育,沒有黃老師洗腦,我們又怎能說問題與現今教育有關呢!那這與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教育有關嗎?自從英國從鴉片戰爭掠奪香港以來,她有否從教育入手,把香港人與中國分離?若有,是如何做到的?
靖海侯:這正是我認為不能將香港問題完全歸咎於教育的一個理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人(英國殖民時代的遺老遺少)是香港問題的始作俑者,也是香港教育問題的始作俑者。而他們沈淪至此,當然跟英國殖民有關係。
李敏妮:2019年,你看到很多什麼守護孩子的60多歲的人,中年漢在街上用粗口辱罵警察,為何這些中年老年人要反中?香港自1840年鴉片戰爭給英國掠奪後,到了我們這一代,根本沒有憤恨悲傷,已經與中國徹徹底底分離了。我們從沒當自己真的是中國人,亦從沒感受過以是中國人為榮。小時候,我們班房前方的牆壁上都掛著穿著華麗的英女皇頭像,這是思想改造,就是說我是你要尊敬的人,我關心你!有一個朋友非常戀殖,他的爸爸痛恨內地,從小就跟孩子說:「英女皇安排的是最好的」。

修例風波期間,「好鄰捨北區教會」發起「守護孩子行動」支援黑衣人。行動成員大多是中老年人,負責站在前線「掩護」。圖片:網上
我們媒體的一個博客說,港英政府想盡辦法令香港市民與內地之間的分岐挖大,方便長久佔領及控製香港這個生金蛋的殖民地,包括不鼓勵簡體字,只推廣廣東話,在學校不教普通話,令香港人對簡體字及普通話非常抗拒。他說「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死抱住他們幾十年前的落後形象,對新中國的進步視若無睹。」再加上黃媒的荼毒,他們對中國人只有嫉妒厭惡,反中情緒便一觸即發。
靖海侯:您說的很對。英國殖民香港,在教育上做了大文章,就是想把香港人與中國分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時,堅持以英語為教學語言。而且,英國人想要的「教育」不只在校園中,他們給香港大大小小數千個地方、街道起的英文名字,本身就是一種教育殖民政策。香港回歸後,英美等國還在香港高校里成立「港美中心」等,一度主導香港大學通識教育。其用心也深,手法也多,對香港今天的教育問題負有重要責任。
今天香港要撥亂反正,迫切需要清除這些余毒。

圖為培正學生在校內唱「獨」歌。國安法立了之後,反動的學生已經成為社會的暗流,蠢蠢欲動。對話接近尾聲,被問到有否信心香港的教育會變的更好,靖海侯說:「我們應對香港教育有信心,而且我們必須要有信心。」
13. 最後,您有什麼願望,希望香港的教育怎樣改變?你有沒有信心香港的教育會變得更好?
李敏妮:過去一年,有消息反映僱主不再聘請本地大學的畢業生,但不是所有年青人也有參加示威的,若果僱主一刀切不考慮本地畢業生,這對沒有參與暴亂的學生很不公平。錯了的學生,若懺悔了和承擔了責任,僱主亦應該給他們機會。
靖海侯:修例風波中,伍淑清曾經痛心的表示,她對香港年輕人已經不抱有期望,認為這是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無法輓救的問題。葉劉淑儀說整治香港教育,可能需要10年、15年。我的觀點與她們有所不同。
我認為:1.亡羊補牢,猶未為晚;2.特區政府有足夠手段應對、處置這些問題;3.中央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是有承諾的,且是有誠意的,對香港年輕人的關懷關心是及時周到的,而這溫情期許一定能被香港社會感知;4.通過修例風波,很多人已經意識到教育的問題,特別是在家庭層面上,讓社會有整體的反思;5.隨著香港整體上的撥亂反正,社會生態的改良,教育會自發調整、適應、跟進。
李敏妮:我們要從多方面入手解決問題。在教育層面上,教育局要有系統地推行公民教育,幫助學生建立良好品格,和思考能力;把中國歷史成為必修科;在老師認證及持續教育裡加入「教學要持平」的培訓。學校要拿出勇氣,懲罰犯錯的學生,從而幫助他們改過。
靖海侯:所以,我們應對香港教育有信心,而且我們必須要有信心。不說為了國家和香港,為了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都要這份信心,並力所能及地參與其改革中,確保孩子可以接受好的教育,心無旁騖的讀書成長,讓他們活在陽光下,對社會懷有善意,對未來抱有希望。
李敏妮:幾天前一個朋友發給我一篇文章,裏面寫到:「學問之道,在於造就一個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要如何立身處世的道理。至於知識和文學等等,只是整個學問中的一部分,並非學問的最高目的。」作者寫到:為學的精神,要做到隨時隨地,在事物上體認,洞明世事,練達人情。
這段說話說出教育的真正意義。要教育變得更好,整個香港社會要明白教育的目的。教育是為了考試拿取第一,找一份好工,還是要培養有思維、有品格的人,將來能夠貢獻社會?
靖海侯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