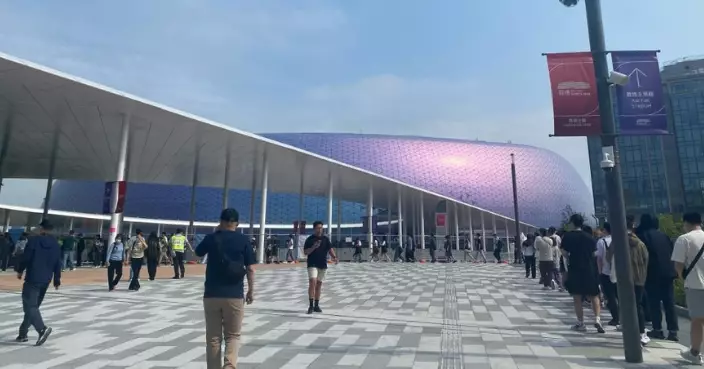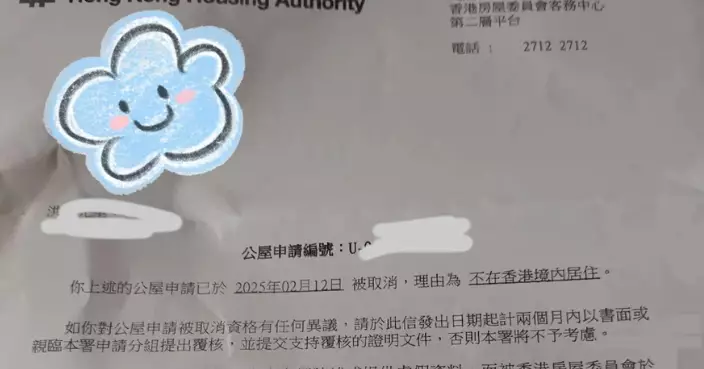失業綜援與其他類別的綜援如長者綜援不同,年齡介乎15至59歲且身體健全的申領人必須強制參與「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即每兩星期或一個月最少求職兩次,並與就業援助主任交代進度和結果,以及每星期安排一至兩天參與義務社區工作。根據政府多份報告,例如時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在2000年向立法會提交的<中期評估報告>,都認為推行計劃有助減少申領失業綜援的個案,亦可以幫助申領人裝備自己及重返勞動市場。
不過,近年有關計劃的成效出現明顯的變化。根據2019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回應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的提問時指出,大約95,000人強制參與的「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只有21.3%成功就業或投身主流教育,至於脫離綜援保障更是僅佔大約4%,反映計劃的實質作用並不理想。令人更加吃驚的是,計劃在推動失業綜援申領人士重投勞動市場的表現每況愈下,例如根據2007年的數字,該年參與計劃人員的成功就業率高達36.4%;直至2012年為止,每年平均成功就業率介乎25%至27%。換言之,我們可以看到「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成效向來不高,即使高峰時期其成功就業率都未能過半;而近年的情況更是漸走下坡,甚至連由政府自行設定的最低目標都未能達到(每年成功就業率25%)。
既然「自力更生支援計劃」成效不彰,我們必須思考兩個問題。一,最根本和核心的問題,究竟計劃有否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計劃存在的理由是否正當。如果計劃的原意及發展是毫不必要,那麼根本不應使之繼續推行。二,如果我們認為計劃應該存在,就必須找出計劃的毛病,以及提出修補的辦法。
「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在1999年正式推行,翻查1998年政府代表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介紹有關計劃的發言內容,政府認為計劃「確保將資源用以幫助社會上真正貧困的人士」,顯示政府的立場,認為失業人士並非「真正貧困」,而他們領取社會福利是資源的浪費,為了有效運用社會資源,便要設下關卡讓失業人士較難取得綜援及推動他們重返職場以自食其力。
在1999年,相關部門再次出席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交代計劃其中一個項目「積極支援就業」的進度。在會議文件中,政府指出計劃的目的,是要失業綜援申領人「認同就業的價值;找出防礙他們就業的原因‥‥‥邁向自力更生的目標」。這段文字反映政府的思維,就是所有符合勞動年齡的健全人士都必須認同和參與勞動工作,勞動不再是個人選擇和自由,而是制度的要求和期望。即使因為受到任何因素影響而陷入失業及申領綜援的困境,也必須盡快投身勞動市場。至於2000年由社會福利署提交立法會有關「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中期檢討報告更加指出,計劃的成效在於「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使更能明白需要重新自力更生;了解就業的重要性」,直接說明就業和勞動是應當履行的個人社會責任和公民義務,甚至將失業人士標籤為不願工作和自力更生的人。
從政府多份文件的措辭可以了解,政府對於申領失業綜援人士充滿歧視和壓逼。正如上述,政府已經假設所有健全且適齡的人士必須工作,靠著自身的力量養活自己,亦即將參與勞動和自食其力這種本來不屬於必須履行的公民責任,突然劃上等號,令失去工作而又申領福利的人感受到無形的社會壓力和內心愧疚。如果有人領取失業綜援,則會被視為沒有就業和自力更生意識的「寄生蟲」,所以政府的「責任」,就是以不同的限制、「思想教育」和服務支援,「開化」和「引導」這班「寄生蟲」進行勞動達致自給自足以實踐公民責任。
其實政府這種對申領福利的失業人士之歧視甚至敵視,是源自於萌芽於上世紀40年代、於70年代興起並沿用至今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思潮。根據社會學家David Harvey的說法,新自由主義具備四個主要特徵:一,強調和重視個人的權利、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作出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選擇;二,強調政府不應該對社會運作作出干預,應該僅僅充當鼓勵私人市場發展和競爭及建立完善司法制度以保障個人權利的角色;三,政府應該鼓勵資本的發展,如減少徵稅、減少貿易和投資限制、增加基建等等,方便商業活動;四,由於政府功能極少,也要尊重個人和市場的選擇,所以政府規模必須盡量縮小,不應該向任何人提供福利,即使原本投入在教育、房屋、社會保障等人類基本權利的資源也應該改由市場分配。
這種強調個人自由,崇拜市場機制的想法,在70年代開始成為各個大國,包括英、美政府奉行的金科玉律,是因為經歷兩次大戰之後,全球經濟蕭條,大量人民失業或生活困頓,各國政府出於人道考慮及政治需要開始建立具規模的社會福利制度,穩定社會。然而,自1960年代起,質疑福利制度的聲音在學術界和政界此起彼落,認為大大減低受助人的積極性,使其過份依賴政府援助,影響經濟發展和增加政府開支。最終,各國開始摒棄「福利社會」(Welfare State)的制度,改為採納新自由主義。雖然這班新自由主義支持者上台執政後,沒有完全廢除社會福利項目,但是大幅改變社會福利的方針與思維,由強調「平等」,即人人有需要都可以申請,改為強調「市場化」或是「工作福利」(Workfare),受助人必須工作或有意願尋找工作才可領取社會福利。
香港在英殖時期已經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所以即使在70年代展開綜援計劃,其規模、待遇等等仍遠較不少先進發達國家為差。而真正促使香港政府改變對失業綜援申領人立場的導火線,是由於香港回歸後面對金融風暴,政府赤字連年,使得政府官員及民間聲音認為政府應該節流,減少支出,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向綜援埋手,將失業人士視為沒有必要領取福利的人,並對這類人士設下各種關卡。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主管陳澤群教授曾經出版一篇名為「香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福利制度」的論文,研究香港失業綜援。雖然其結論令人哭笑不得(認為因為香港沒有民主普選所以政府可以肆意改變失業綜援的方針,哈哈),但是他有一個觀點非常正確,就是社會福利是一種公民權利,其原意是幫助社會的弱勢或是不幸的人,使他們可以過著文明發達社會中可接受程度最低的生活。對於此等處境慘酷的人,政府不但沒有積極提供援助,反而是設置各種條件使之難以領取福利以解燃眉之急,實在是極不人道的做法。
事實上,市民面對失業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施政不彰的後果。例如,政府過份鼓勵商業活動,鼓勵資本競爭和累積,最終企業為了追求利潤和效率極大化而以改用自動生產、轉移生產地點、整頓公司規模等理由而縮減人手,最終製造大量人士失業;政府在教育上錯放資源,未能培養一班技能或知識上適切勞動市場需要的人才,以致競爭力低而無法覓得工作;或是政府及大型企業過份依賴外判制度,變相壓柞基層工友的工資,使他們無法賺取足夠維生的收入而寧願申領綜援以獲取基本保障等等,其實是政府政策的後遺症。作為問題的始作俑者,政府向失業人士提供支援實在責無旁貸,但是政府反而將失業的責任,歸咎於當事人沒有承擔公民責任及自力更生的意識,將之視為負擔,並想方設法地使他們離開福利保障,明顯是諉過於人。
當然,筆者不會否認失業問題存在個人原因,如工作表現欠佳等,但是造成大量人士失業並要申領福利的原因,除了政府施政問題之外,更大程度上與外在的經濟、社會形勢有關。例如回歸初期的金融風暴、2003年的沙士事件、2008年的金融海嘯至近兩年的新冠疫情等,都重創經濟發展和相應的就業機會。市場上本來就缺乏足夠的職位,但是「自力更生支援計劃」仍然強逼申領人按照規矩辦事,或是執行無助提升競爭能力的社區任務,如到海灘執拾垃圾等,最終只會促成三種結果:一,大量失業人士被逼繼續留在求職市場,眾人為了得到職位而相應降低待遇要求,即使成功離開制度也是極為廉價且受到嚴重剝削的員工;二,原本仍有工作的人因為求職市場人手供應過多而被取代失去工作,最終即使有人成功求職而無須再領取福利援助也好,失業問題實際上根本沒有改善。三,一班失業人士因為在「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要求裡沒有得到具市場價值的培訓,無從提高競爭力,加上長期失業,反而更難找到工作,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計劃成功就業率及離開綜援保障比例偏低的原因。
雖然,政府美其名地表示「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可以減少政府開支及更好運用公共資源,但是,必須指出失業綜援從來不是綜援計劃或整個社會福利制度裡的多數。在1998年,即是推行「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前的一年,各類綜援個案合共約21萬宗,在金融風暴的影響之下,當中也只有26,000宗個案屬於失業綜援,比例大約是12%。時至今日,綜援個案超過22萬宗,而申領失業綜援的個案不足2萬宗,佔比甚至不足一成。近年政府每年投放超過900億在社會福利署應付各項開支(例如長者生活津貼、資助安老院舍、兒童及青少年支援服務等),在如此龐大的支出下,即使能夠將所有失業綜援申領者剔出保障範圍,對於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可謂杯水車薪。
不論是發達國家如澳洲、德國,或是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等,以「工作福利」思維提供失業保障所取得經驗都是大同小異,就是福利申領人認為所有由機構提供的就業輔導都是浪費時間,對求職根本毫無用處。面對硬性規定必須定期出外求職以滿足制度要求,加上需要頻密應付繁瑣的事務,如與福利機構職員會談交代進度、每星期參與義務社區工作等等,福利申領人容易失去自信和情緒低落,對鼓勵他們求職反而是事倍功半。
既然壓逼,包括政策上標籤失業綜援申領者是缺乏自力更生意識的人、理念上強逼他們接受和認同必須勞動、制度上要求他們必須達到定期求職及參與義務工作,根本難以協助他們重投職場,甚至對他們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困擾,足證這種政策思維好應立即修正。筆者強調,本文並非反對政府以任何形式協助失業綜援申領者,只是反對政府採取有關計劃的原意和以強硬且弄巧成拙的方式,逼使他們離開綜援保障和重投勞動市場。政策的目標,不應該是計算多少申領者變成勞工及可以節省多少開支,而是以鼓勵和開放的態度接受和配合不同申領者各自的需要。
第一種鼓勵的方式,是使申領人能夠掌握勞動市場吃香職業技能的「技能鼓勵」。現時「自力更生支援計劃」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過分催谷失業綜援申領人東奔西撲地定期求職及參與社區義務工作。然而,大多數人士失業的原因,正是缺乏市場需要的職業技能,以致失去競爭能力。但是基於現行制度的要求,為了避免無法領取綜援,他們被逼硬著頭皮應付無助培養勞動市場相關的技能的社區義務工作,結果他們依舊無法提升自身價值,擺脫失業就難上加難。因此,與其硬性要求定期求職和參與義務工作以維持申領者的工作積極性,倒不如改為鼓勵他們提升技能,建立一門他們既感興趣又可以發揮市場效益的技術。
當然,政府現時也有透過僱員再培訓局、建造業議會為失業綜援申領人提供再培訓課程,不過,相關課程都是職業、甚至是行業導向,課程定位亦以低技術、低收入工作為主,政策目標更多是考慮舒緩部分行業人手短缺的問題,多於真正為每個申領者打造個人化的技能培訓以鼓勵工作。因此,政府除了提供認可機構的職業培訓以外,亦應該尊重和重視每個申領者的背景、需要和想法,承認和提供非職業導向的培訓,例如藝術、運動、音樂、語文等等,使他們掌握有關技能並在靈活運用下逐漸發展成相關技能的專業人士,以達致重投勞動市場的效果。
另一種鼓勵的方式,當然是實際的物質鼓勵,即是放寬失業綜援申領者的工作入息豁免的金額。為了鼓勵申領者工作,同時減輕他們對於一旦離開綜援保障便會失去各種福利如免費公共醫療、租金補貼等的憂慮,綜援制度容許申領者從事薪金不超出某一水平的工作。不過,由於申領者已有一定收入,所以當局會在提供入息豁免下,適量扣減申領人部分綜援金額,避免資源浪費。在2021年之前,有關的入息豁免為首800元全數不用扣減綜援金額、此後3,400元則扣減入息之一半(即可獲最多1,700元的豁免)。換言之,收入4,200元以上的申領人可獲最多2,500元的入息豁免。按照這個制度,假設某位單身的失業綜援申領人從事一份月入5,000元的工作,由於其綜援標準金額為2,615元,即是該名人士會因為工作而只剩115元的綜援補助及5000元月薪,入息水平只是香港一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6.8%,接近香港的貧窮線水平,生活仍然相當艱難。由於部分申領者擔心從事人工稍多的工作便會失去全數綜援福利,而工作後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不見得大幅提升,所以理所當然地不會積極就業。
2019年,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承認入息豁免的金額多年沒有檢討,是阻礙申領者求職的重要因素之一,故由今年2月開始,入息豁免將會改為首1,200元全數不用扣減綜援金額、此後5,600元則扣減入息之一半(即可獲最多2,800元的豁免)。換言之,收入6,800元或以上的申領人可獲最多4,000元的入息豁免。我們再次引用剛才的假設,即某位申領人從事一份月入5,000元的工作,該名人士便會被扣減1,900元的綜援金額,總收入為5,715元,入息水平為一人家庭中位數的63.5%,雖然已經高於歐美國家對貧窮線的定義(入息中位數的60%),但是生活仍然並不見得輕鬆,對於推動失業綜援申領者求職吸引力依然不算太大。再者,政府從來沒有承諾每年檢視豁免金額水平,即是有關水平並不會接照通脹等因素而調整,長遠而言對願意工作的申領者不利。因此,提升入息豁免金額,並每年進行調整,方是在物質上的最佳誘因。
最後,政府應該改變對工作的定義和看法,以開放、開明的態度看待勞動的價值。現時政府對於勞動的看法,除了認為是所有健康和適齡人士務必實踐的公民責任之外,就是必須在公營或私營機構任職並發揮經濟價值以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然而,正如由香港城市大學及理工大學兩位教授撰寫的論文<<重新思考香港單親媽媽的社會保障制度>>(Rethinking social security reform for lone mothers in Hong Kong)指出,將勞動與從事能夠賺錢養活自己的工作是偏頗狹隘的想法。以單親媽媽為例,在家庭中照顧未成年的子女、打理家中大小事務其實同樣屬於勞動。雖然家務不會對社會產生直接的經濟價值,她及其家人也不會因為完成家務而得到任何報酬,但是這種勞動對於社會正常運作和發展而言是必須的。現時政府不但不體恤料理家務或照顧家人的需要,甚至貶抑他們勞動所發揮的社會作用,執意要求他們從事有實際工資和經濟效益的工作,實在是不近人情且思慮不周。因此,承認和肯定從事家務或義務工作為勞動,避免強逼該等人士必須重投勞動市場,同樣有助優化計劃。
政府必須接受,失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無可避免的現象,部分更是政府決策失誤和資源錯配的結果。對於有經濟需要的失業人士,政府不應該加以歧視和壓逼,千方百計將他們拒之於門外,相反,容許他們有個「避風港」,並以適當計劃提升他們工作的能力和意願,才是這群不幸的人、政府和整體社會「三嬴」的局面。
黃遠康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