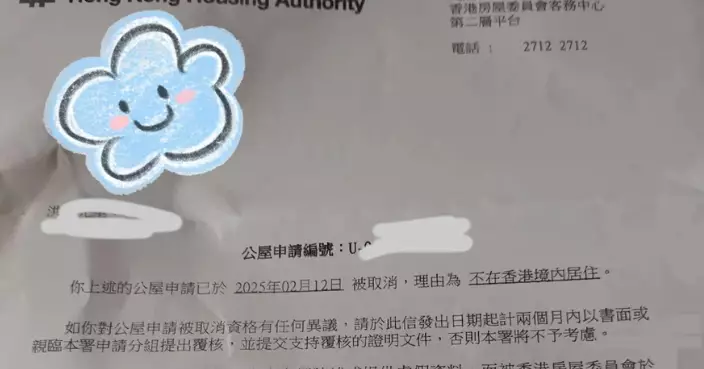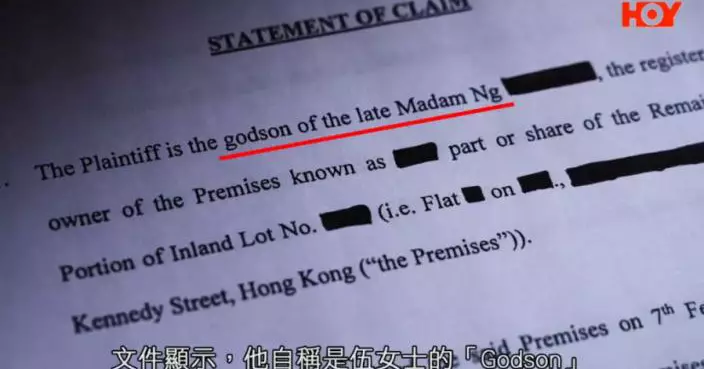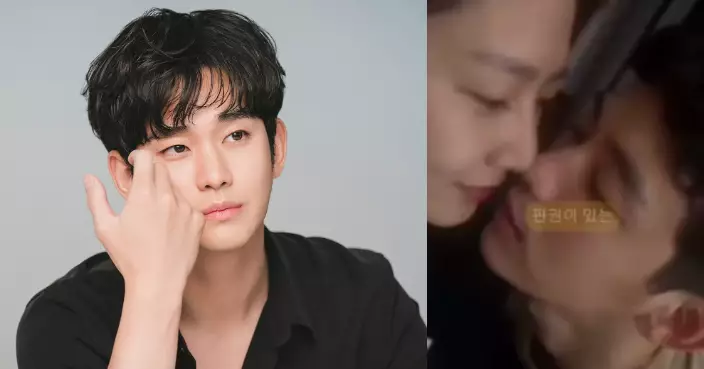楊開慧與毛澤東(資料圖)

江青(左)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我去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採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髮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髮,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面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里,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面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里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里、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里”。
鄭君里,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繫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里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蘋,本是鄭君里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里(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蘋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里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蘋,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里為司儀。
黃晨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著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歷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騙騙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里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江青(中)林彪(右)、葉群在一起(資料圖)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里回到家裏,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里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著面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里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裏。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
鄭君里明白,這是張春橋找他談話的真正目的,他從張春橋的話中聽出,顯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別人不會知道那封信的。
當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在側。
據梁國斌回憶:
“一九六六年六月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曾對我說,江青現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鄭君里家,我要找鄭君里談一次,為慎重起見,你也參加一下。我答應了。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時我在場……
「張春橋對鄭君里說,現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完全答應。」
鄭君里和黃晨一起在家中翻找,總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廠里轉給張春橋。
梁國斌回憶道:
「事隔約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對我說,鄭君里那裏的信件、照片等交出來了,已轉交給江青,她當場燒了。」
這麼一來,鄭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過了些日子,張春橋又一次找鄭君里談話。
這一回,張春橋的臉上烏雲密佈,彷彿馬上就要發出閃電和雷鳴。
他不再繞彎了,單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為什麼不交出來?」
從話語中可以聽出來,顯然,江青已經看過鄭君里上一次交給張春橋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了。」鄭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憶一下,把信找出來。」張春橋依然不放過他。
鄭君里回到家裏,憂心忡忡,他早就銷毀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來,而江青又緊追不捨。
黃晨和他翻箱倒櫃,鄭君里向來很重視保存創作資料,便於寫作,他保存了許多三十年代電影書報、剪報。凡是其中涉及藍蘋的,都一一交出。
黃晨還找出了一張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納、藍蘋、鄭君里,她。
她記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們在霞飛路(淮海中路)萬籟鳴兄弟所開的「萬氏照相館」里拍的。

1935年的藍蘋(右)與王瑩(資料圖)
鄭君里見到這張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黃晨慮事比丈夫仔細,只見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納。鄭君里會意,讚許地點了點頭。因為如果不剪去唐納,更會招惹麻煩。
再也找不出別的「防擴散材料」了。鄭君里深知,這一回的材料仍沒有那封信,江青勢必不會放過他,於是,鄭君里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說明信件“沒有保存,只是理出幾張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請你處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氣,她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為了避免她的糾纏,他在信中還寫道:“運動之後,我們搬到農村去落戶,搞搞文化館的工作……”
雖然鄭君里已經退避三舍了,然而,他並沒有從江青的記憶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視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殺人,這「刀」便是葉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七歲的生日,成為紅衛兵的盛大節日。一百五十萬紅衛兵雲集天安門廣場,使那裏成為一片紅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離毛澤東只咫尺之遙,揮動著小紅書,向紅衛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權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她見到葉群。葉群邀她到毛家灣走走,她答應了。
三天之後,江青出現在毛家灣林彪寓中。
江青和葉群在微笑中,談成一筆骯髒的交易:「你替我撥去眼中釘,我幫你幹掉私敵。」
於是,江青說起了鄭君里,說起了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一封信。
於是,葉群通過吳法憲,電召江騰蛟火速來京。
於是,十月八日深夜,一夥不速之客,光臨上海武康大樓鄭君里家中……
據黃晨回憶,在抄家的時候:
「不准任何人進出,對我們搜身,叫我們把所有的首長的文字東西都拿出來,把我們的書翻了一地……把君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創作手槁、資料搜刮一空,連我的小兒子從幼兒園到高中作業的成績報告單都拿走了。……」
「大抄家後,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監獄裏,君里同志受到慘無人道的嚴刑逼供,僅兩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麼信
在採訪黃晨之前,我曾聽到一種關於那封信的傳說。
據說,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
這封信,是因毛澤東寫了那首《蝶戀花(答李淑一)》引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報》連載了《訪李淑一》一文,記述了記者訪問當時在上海老友鍾淑賢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詳細談及了毛澤東寫作《蝶戀花》的經過。可以說,李淑一的這段話,是關於毛澤東為什麼寫《蝶戀花》的最權威的解釋:
“李淑一同志說,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節,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賀年信去,因為我已經有三年沒有寫信給他,算是向他請安的。還給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舊作求教。當時(指一九三三年)因為道路傳聞,說直苟已不在人間,有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直苟回去,樣子非常狼狽,我哭泣著醒來,和淚填了一首《菩薩蠻》,原詞是這樣的:‘蘭閨索寞翻身早,夜來觸動離愁了。底事太難堪,驚依曉夢殘。徵人何處覓?六載無消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同時,我還要求他把他從前寫贈楊開慧烈士的一首詞寫給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開頭就說:‘惠書收到。過於謙讓了。我們是一輩的人,不是前輩後輩關係,你所取的態度不適當,要改。’(引者註:《新民晚報》所登毛澤東致李淑一信,個別字句有誤,引者已據《毛澤東書信選集》更改。)意思是我不應當用‘請安’的字眼。我的《菩薩蠻》他看了,信里說,‘大作讀畢,感慨系之。’他沒有把以前贈楊開慧烈士的詞再寫出來,他說那一首不好,‘有《遊仙》一首為贈’,還說,‘這種遊仙,作者自己不在內,別於古之遊仙詩。但詞里有之,如詠七夕之類。’這就是大家已經讀到的‘我失驕楊君失柳’那一首《蝶戀花》。
「這首詞寄到學校後,(長沙)第十中學(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單位。)的同學爭相傳誦。湖南師範學院的學生也知道了,他們想在校刊上發表,寫信去請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發表?後來主席親自複信,同意發表,只是把題目改成了《贈李淑一》。後來,《人民日報》、《詩刊》和各地報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澤東的戰友,犧牲於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戰爭。楊開慧為毛澤東夫人,犧牲於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話,把毛澤東寫作《蝶戀花》一詞的前後經過。說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澤東對柳直苟烈士、楊開慧烈士的懷念,寫下「我失驕楊君失柳」那樣充滿深情的詞句。

1936年轟動一時的三對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為:葉露茜與趙丹,藍蘋與唐納,杜小鵑與顧而已。後排則為證婚人,自左至右依次為:鄭君里、沈君儒、李清(資料圖)
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戰友之情。然而,卻觸動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經。江青當著毛澤東的面狂叫:「你懷念楊開慧,我想念唐納!」
江青一氣之下,給鄭君里寫了一封信,打聽唐納在國外的地址……
據傳,江青要追索的,便是這封在一九五八年寫給鄭君里的
當然,這僅僅是「據說」、“據傳”而已。因為關於那封信,一直是一個謎:不論是對張春橋或者葉群面授機宜的時候,江青只是說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鄭君裏手中,並未談及是一封什麼內容的信件。何況葉群已死,張春橋則以緘默對抗,無法從他們那裏查清江青千方百計要追回的是什麼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鄭君里知。
不過,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別法庭開庭審問江騰蛟時,江騰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問:「你到北京以後,葉群怎麼給你具體交代任務的?」
答:「葉群跟我講,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鄭君里、顧而已他們手上,現在要把這封信收回來……」
這裏提及的顧而已,顯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尋的,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信——正因為這樣,她指使張春橋找鄭君里談話,並沒有找顧而已談話。
江騰蛟的交代,明確地說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審問時,審判員高斌特地追問了一句:
問;「到底要搜查江青什麼時間的信?」
答:「五八年,我記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樣會“有一封信落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鄭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寫信給鄭君里!
江騰蛟的交代,清楚地證實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
在筆者訪問黃晨時,她說鄭君里怕惹事,早在張春橋找他談話之前,已經燒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為這樣,張春橋一直追逼之下,他也無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寫給他的信。
黃晨還回憶,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還曾給鄭君里寫過一封信,事關她、唐納和另外一個人。
要說清楚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從頭講起……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