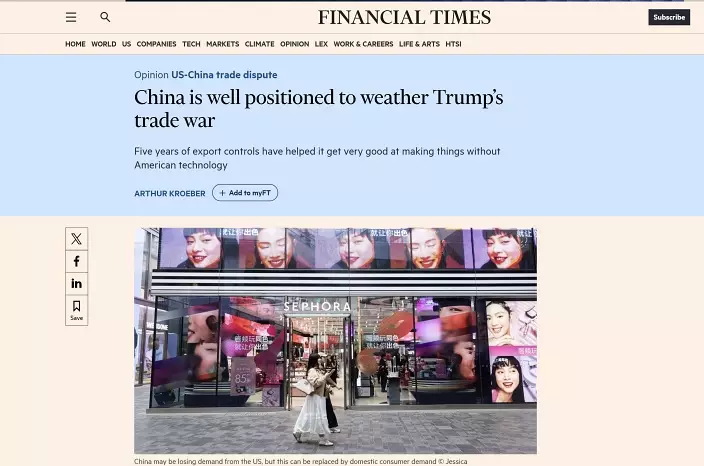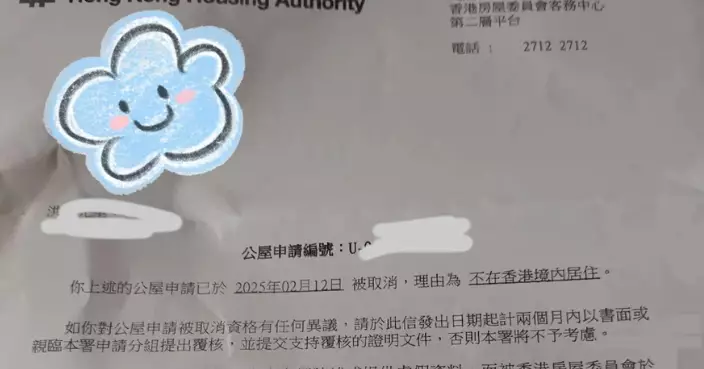「美版拼多多」Wish於2012年推出,比拼多多還早了兩年時間。這個原本有望成為美國下沉市場商業神話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破滅?

Wish創始人Szulczewski。
2016年底,廉價電商Wish的創始人Szulczewski蹭了一波特朗普的熱度:事實證明這個國家的精英忽視了「沉默的另一半」(invisible half)。
據公眾號「遠川研究所」,Wish主打廉價白牌商品,廣受美國下沉市場的喜愛,長期被各路分析師稱作「美版拼多多」,兩者的類似之處還有很多,比如都從移動端起家、注重算法推薦。
2017年,Wish斥資3600萬美元拿下洛杉磯湖人的球衣廣告,理論上勒邦占士工資裏有Wish的一份功勞。

勒邦占士的球衣。
2018年,Wish下載量超越亞馬遜,位居全球購物APP首位;2020年底,Wish用戶破億並成功上市。創始人Szulczewski聲稱,Wish將跟隨亞馬遜和阿裏巴巴的步伐,成為下一個萬億規模的電商平台。
Szulczewski要麽是高估了自己的水平,要麽是高估了美國五環外老鄉的能力。從2016年至今,Wish連虧七年,市值較高點縮水了99%,在今年2月被新加坡電商Qoo10以1.73億美元的白菜價打包帶走。
在整個2023年,Wish的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商品成交金額)只有21億美元——距離萬億夢想差了99.8%。
Wish上綫於2013年,比拼多多還早了2年。
在下沉市場的戰略上,Wish完全預判了拼多多的預判:Wish客單價僅有20美元,遠低於亞馬遜和eBay。平台上的爆品大多為「1+1」産品,即售價和運費都是1美元。高達75%的Wish用戶承認,自己就是喜歡便宜貨。
創始人Szulczewski曾引用過美聯儲數據,41%全美家庭掏不出400美元的現金,因此為「支付不起120美元亞馬遜Prime會員」的「鐵銹帶」老鄉打造一個電商平台,是Wish義不容辭的職責。

Wish的兩名創始人,Szulczewski與張晟。
老鄉們的需求,自然需要性價比産品來滿足。為此Wish大幅降低了中小賣家的入駐成本和門檻:平台不收開店費用、也無需繳納保證金,賣家只要提供身份證就可以上架商品。
對Wish來說,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能滿足大規模的低價産品供應:2019年,Wish賣家數量突破100萬大關,94%賣家都來自中國,其中廣東賣家占27%。
珠三角賣家和鐵銹帶老鄉聯手打造了一個美國版的下沉市場商業神話——2018年,Wish下載量超越亞馬遜,成為全球下載次數最多的購物軟件,銷售額攀升至美國前三;2020年,Wish月活正式邁過了一億大關。
但降低賣家入駐門檻帶來的隱患,也在此過程中開始悄然暴露。
在疫情期間的2021年,美國電商市場增速超過26%,電商集體嗅到了彎道超車的機會,彼時亞馬遜和ebay營收雙雙大漲。
Wish同樣想大幹一場,結果却被大幹一場:全年營收僅為20.85億美元,同比下降18%,就連用戶留存都出現了下降。
過低的賣家入駐門檻變成了一顆在2021年爆炸的定時炸彈,願意刷單換好評的都算金牌賣家;大量劣迹賣家發假貨甚至空包,等到投訴落地早已人去店空。

Reddit用戶發帖稱:「千萬不要在Wish上買厠紙」。
法國當局就曾多次對Wish進行調查,結果發現95%的抽查産品不符合法律標準,更有45%的玩具、90%的電器甚至帶有危險性,在Wish下單刺激指數堪比開盲盒。2020年,法國直接把Wish排除出了國內市場。
面對用戶和監管的責難,Wish再度祭出昏招:加大罰款力度。
針對違規行為進行罰款無可厚非,但問題出在了Wish純粹用罰款代替了管理。
一方面,罰款並沒有杜絕劣迹賣家的存在。這些賣家一旦被罰,就會迅速用其他身份證另開新號,繼續投機套利,深得「敵追我跑」的游擊戰精髓。
另一方面,Wish在罰款中很難界定邊界,誤傷了大量的「守法」賣家——因為物流慢了被差評,背鍋挨罰的是賣家;有時甚至因為上架商品太便宜,商家也會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罰。
曾有一位服飾類賣家稱,自己在2018年初貸款了100多萬用於擴大團隊,然而伴隨著Wish各項罰款愈加「離譜」,賬上的貨款迅速减少。最終自己辛苦奮鬥整兩年,淪落到賣房還貸的境地。
更加哭笑不得的是,由於Wish的母公司在美國,中國賣家想要討回罰款,還得去美國當地法院提起訴訟,維權的成本和難度都指數級上升。
眼看著隔壁亞馬遜賣家發家致富搬進了深圳灣一號,而自己却屢屢被Wish放血,以至於有賣家懷疑罰款並非Wish的管理工具,而更像是創收手段。
2019年初,Wish每月僅靠罰款就能進賬300萬美元。

Wish「亂罰款」現象一度震驚央視。
一邊是平台罰款標準飄忽不定,另一邊商家却往往申訴無門,「劣幣驅逐良幣」如同教科書般上演:2022年,在一次跨境賣家抽樣中,仍然留在Wish的賣家僅有20%,已經選擇離開的則高達35%。
大量優質賣家另覓他處,反而「提純」了Wish的劣迹賣家含量,這就導致用戶體驗陷入了持續下降的惡性循環。
曾有一份針對超過1.6萬Wish用戶的調查問卷,其中有23%的人聲稱商品與預期相距甚遠。充斥社交媒體的負面言論,也進一步加速了用戶留存和活躍度的下滑。
Wish自己吞下了最後的苦果。到2022年末,Wish先是把月活跌到了僅剩2000萬,隨後是營銷開支跌了80%,最終連帶整體營收暴跌73%,全年虧損3.84億美元。
意識到問題嚴重性的Wish終於著手自救,但它的中國同行已經殺過來了。
2022年2月,Wish取消了賣家的自行注册,開始實行邀請制;在這之前又推出了「Wish Standards」計劃,從産品質量、客戶評論、退款率等多個維度,對商戶進行評估以進行流量分配。
Wish的策略是清晰的:上綫邀請制,堵住了低質賣家的繼續涌入;而「Wish Standards」計劃,則可以將用戶體驗不佳的賣家清理出去。
但這依然無法抵抗Wish螺旋下墜的重力。在最近一次2023年3季度的財報中,Wish季度收入僅為6000萬美元,不及去年同期一半;而平台賴以維繫的月活用戶,更是只剩下了1100萬。
多年高額的營銷支出化為烏有之後,Wish母公司選擇套現離場,已經成為了最後的止損。

wish活躍用戶數近年大幅下降。遠川研究所製圖
Wish自誕生之日起,曾連續押中手機電商、推薦算法、下沉市場、社交流量等一系列的時代彩券,但最後的勝利者反而是拼多多。
2022年9月,拼多多旗下跨境電商Temu,携「全托管模式」登陸北美。根據SensorTower的數據,Temu全球月活在去年10月就已經來到了約1.3億。從這個角度來看,Temu僅一年時間就抵達了Wish未曾企及的高度。
Wish的低價,本質上來自簡單粗暴的降低賣家門檻,始終沒有脫離「撮合交易」的語境。但中國跨境電商的成本控制,實際上來自對供給端的深入與掌控。
全托管模式下,國內賣家發貨必須經由Temu國內倉檢驗,才會由平台發往海外。跨境電商長期存在的品控問題,由此被打上了補丁。

Temu國內倉。
而更早出海的SHEIN,更是把從原材料採購、服裝設計,再到釋放訂單、履約售後等大量環節,牢牢攥在了自己手裏。
這種情况下,賣家承擔的職責無限接近於單純的生産和供應,大量的運營工作都被電商平台攬在手裏。而平台支付的成本也相當驚人,一份調研紀要顯示,Temu每天會用到1~3萬人來分揀打包。與此同時,國內的客服團隊也長期穩定在大幾千人。
無論是大規模倉庫和客服團隊的組建,還是針對數萬人團隊的管理,對Wish這家美國公司來說,屬實有些超綱。
在把人管起來這件事上,還是我們東亞人更在行。
深喉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