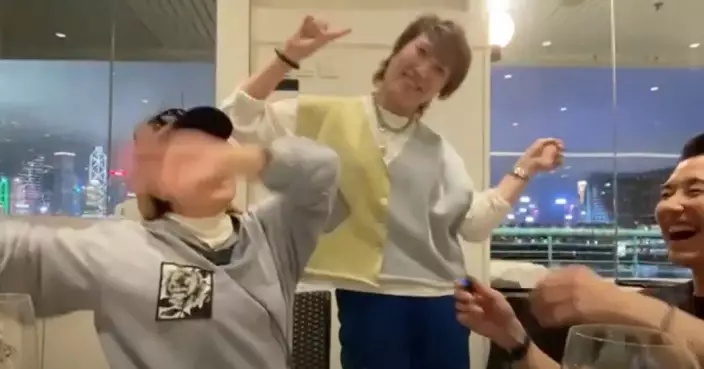「35+顛覆案」判決後,不少反對派議員罪成。1989年的六四事件過了35年,海外仍有人進行悼念。這兩件事讓我想起一個「泛民」議員的故事。
21年前,就在2003年反對23條立法大遊有行過後,在一場飯局中,我恰巧坐在一個泛民立法會議員的身旁,和他聊起當時的時局,他情緒十分高漲,痛罵香港的民主發展不前。他當時意氣昂揚地說,「你看人家鐵幕解體10多年,用震盪療法,改為市場經濟,國家快速發展,掀起一片民主氣象,好像我這個年歲(他當時30多歲),很多東歐的民主派已經做了政府部長,甚至政府首長,匈牙利的歐爾班30多歲當上總理,捷克的哈維爾50多歲當上總統,他們甚至已經任期結束下了台,但香港民主派卻完全沒有上台的機會。」
我對他這番話印象深刻。當時的反應已經是,這班泛民議員口裏說得漂亮,最後亦只是想上台執政而已。但他這句「30多歲當總理」的說話,就一直記下來了。我是讀政治學的,當時心想真是找些革命青年來當政府領袖,全盤西化,就可以令國家發展起來嗎?真的這樣簡單?35年過後,這個問題已經有答案。
在幾十年美國和蘇聯冷戰時期,在親蘇的東歐陣營中,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是略為市場化的國家,經濟發展較好。到1989年鐵幕解體後,本來以為這幾個國家,底子較佳,會有更好發展,但結果事與願違。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歐洲不斷東擴,將這些前蘇聯陣營國家吸納其中,和美國關係不好的國家,就被煽動起國內的民族矛盾,將一個個國家分解成了很多個國家。南斯拉夫的狀況更加悲慘,鐵幕瓦解後國家經過第一波分裂,而最大共和國賽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又和美國關係惡劣,美國就不斷分割後來的南斯拉夫聯盟。最後南斯拉夫一個國家變成7個國家,主體民族塞族組成的塞爾維亞現在人口大約700萬,比香港人口還要少。而最後從塞爾維亞分拆出來的一個國家科索沃,只有美國和歐洲承認,在地球上沒有太多的存在感,但就和塞爾維亞鬥爭不休。捷克就一分為二,變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有幸保持國土完整,皆因早期的匈牙利比較親美。
故事說到這裏,難免就要說說歐爾班。在鐵幕解體的年代,歐爾班剛從匈牙利的羅蘭大學法學院畢業,之後在1989年到牛津大學修習政治學,然後回國從政,是一個典型西方培養的東歐革命領袖。他早在1988年已參與創建了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青民盟),是當時反對共產主義的前沿組織,是東歐劇變的主要推手之一。1990年,匈牙利推翻社會主義政權後,歐爾班獲選成為匈牙利國會議員。8年之後,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在議會中取得148席,成為第一大黨,歐爾班在35歲之年,已經出任匈牙利總理。

年青時的歐爾班是一個學運領袖。
不過,歐爾班的從生涯,經歷從左翼到右翼的蛻變。他做完一屆總理之後,大選失利落任,在野8年,到2010年再當選總理,逐步擺脫親美路線,開始變成右翼。
如今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和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是歐洲陣營中最親華的領袖。由極端反共到轉向親華,這是一種鐘擺式轉變。或許經過 30多年的國家發展,特別是他們的國家經歷了西方的震盪療法,一夜間進入市場經濟和民主選舉後,都找不到發展的出路。最後變得親華,也不單是想加大和中國的經驗合作,更希望借助中國的發展經驗,探索到國發展新路向。

現在的歐爾班。
在1989年的浪潮當中,美國列根政府發動這場顏色革命,主要想推翻蘇聯。但對中國亦帶來附帶傷害,反政府浪潮幅射到京城,趙紫陽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想要馬上全盤西化,結果事敗收場。也幸好中國沒有走上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同一樣的道路,否則中國或許已變成10個國家了。
大浪淘沙,那個泛民想做部長的故事,如今已成笑談。
或許歐爾班的故事更有警世意味,35歲當上總理並不重要,能否引領國家走上發展之路,才真正的重要。
盧永雄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特朗普的瘋狂加關稅行動,終於來了。特朗普自稱這為「解放日」,恐怕這是美國「衰退日」之始。
特朗普大加關稅,比市場原先想像的更激進。美國宣布對歐盟成員國在內的180個國家和地區,全面徵收所謂「對等關稅」,特朗普是胡亂弄出一個其他國家向美國徵稅的「關稅+非關稅壁壘稅率」數字,然後所謂減半徵收,得出瘋狂的加稅數字:對中國再加稅34%(特朗普這一任內已對中國加徵20%關稅,新加稅是疊加徵稅),對歐盟加稅20%,對日本加稅24%不等。特朗普聲言,會全面設定至少加10%的加稅基準。
特朗普瘋狂加稅舉世嘩然,加關稅的直接效果是美國聯邦稅收的確會大幅增加。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2024年美國商品入口總額3.3萬億美元,同年貿易赤字1.21萬億美元。假設加稅之後,美國消費者仍然消費入口貨,生產者仍然要入口零件去生產,美國進口並沒有巨額暴跌的話,以估計平均加稅率20%計,特朗普加稅會令聯邦稅收增加6600億美元。
特朗普曾經說過,加關稅會帶來上萬億美元的收入,用於減稅或者補貼兒童教育,重現19世紀關稅支撐國庫的模式。而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就說,單是汽車加關稅,每年就可以為美國帶來1000億美元的收入,其餘商品再貢獻6000億美元,估計加關稅可以令聯邦收入每年增加7000億美元。這個數字和上述6600億美元的估計貼近。
問題是,加關稅會產生什麼效果,誰支付這些關稅呢?
要分析這個問題,就要從特朗普的思維入手。特朗普經常掛在口邊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理想是恢復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經濟崛起的黃金時代。當時英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緊跟其後,正由一個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全面轉型階段。那個年代,美國增加關稅的確扮演了推動工業的角色。美國經歷一段高關稅的搖擺期後,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聯邦政府急需籌措戰時經費,國會不斷提高美國關稅,推出《莫里爾關稅法》,令關稅加到49%。到1890年推出《麥金萊關稅法》,該法案大幅提高了工業產品的關稅,尤其是羊毛、毛紡織品和棉紡織品,加大了對相應工業的保護力度。美國全面向工業化過渡,造就了經濟的黃金時代。1914年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不過,到了1929年,美國故技重施,推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2萬多種進口商品平均加徵40%關稅,試圖保護當時已經開始陷入大蕭條的美國國內經濟,結果觸發全球貿易戰,令經濟衰退加劇,最終導致全球貿易萎縮,到1933年,全球貿易減少66%。美國當年是成也關稅、敗也關稅。
從美國早年加關稅成功的經驗來看,主要因為美國當時是一個新興國家,有廣闊的廉價土地,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有大量新移民勞動力湧入,19世紀末接納了2500萬個新移民,還未計算之前一直輸入的大量廉價黑奴。在這些比歐洲優秀的生產條件之下,加關稅好像按下開關鍵,將歐洲的產業移植到美國,因為美國的生產條件其實比歐洲好。另外,當時全球化的程度很低,國際貿易只佔美國GDP的大約7%,加關稅對國內物價影響輕微。
不過,如今已今非昔比。全球高度融合,美國所有的生產成本都極其昂貴。根據美國勞工局的數字,2023年美國製造業平均工資含福利計是35美元,遠高於中國的每小時6美元工資,以及越南的2美元工資,再加上工會勢力盛行,令工資只升不跌。這種差距令到美國根本不可能做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業等。即使在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如汽車、機械等,由於美國已經廢棄這些產業多年,大量缺乏技術工人,而且美國的人口已相當老化,2023年美國製造業已經有50萬個崗位空缺,同時特朗普也反對輸入勞工,想趕走過百萬非法移民,即使製造業想在美國重啟,勞動力何來也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特朗普想像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打開了徵收關稅的按鍵,美國不能如100年前那樣重建製造業,但聯邦政府的確可能多收7000億美元的關稅,但由於美國對各國廣泛徵稅,即使對中國的徵稅率特高,對其他製造業密集國家的稅率也便宜不了多少,美國入口商面對1.無低稅進口替代途徑,2.本土製造業亦接不上來,所以最大的可能是美國的入口商和消費者要「硬食」這7000億加稅。據耶魯大學的預測,特朗普的所謂「對等關稅」實施之後,其他國家很大機會報復,美國個人消費的價格升幅將會擴大至2.1個百分點,實質GDP增長率會下降1個百分點。
特朗普這樣濫徵關稅,如果沒有阻止貿易的效果,美國人貴貨照買,只是美國自己捱通脹,這還好一點。如果真的有阻止貿易的後果,美國大幅減少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貿易,脫鈎斷鏈,後果嚴重。
股神巴菲特早前接受CBS訪問時表示,懲罰性關稅可能會引發通脹,並損害消費者利益。他坦言自己對關稅有很多經驗,「某程度上,關稅是一種戰爭的行為」。
巴菲特說得對,貿易結束,就是戰爭開始,無論冷戰甚至熱戰,大家都可以放開手打,沒有顧忌了。不知天天大呼「美國贏了」的特朗普,有沒有想清楚後果呢?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