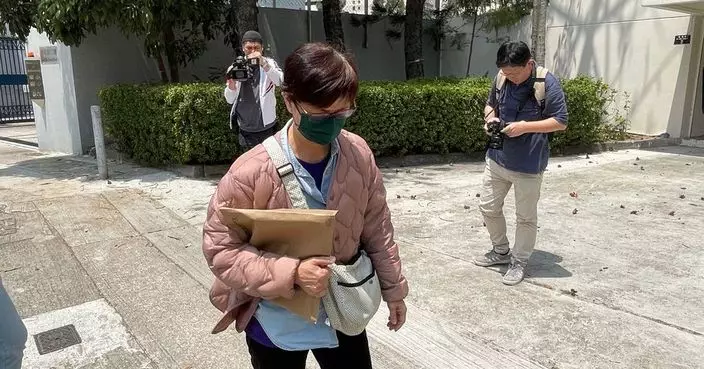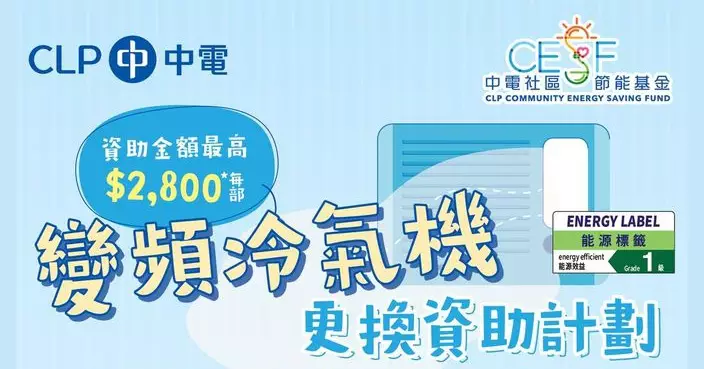今早看報後回想中二上歷史課的一幕,當時講到唐朝「玄武門之變」的故事。唐高祖李淵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附近與太子李建成衝突,結果把李建成和四弟齊王李元吉殺死。不久之後,李淵禪讓帝位,李世民登基,成為唐太宗。歷史講到太子李建成如何昏庸,組成太子黨逼害李世民,李世民被逼殺兄。
當年的我,對此已經十分懷疑。李世民後來成為極其成功的皇帝唐太宗,成功到中國人被稱為「唐人」。按傳統的儒家思想,殺親兄弟、逼父退位,都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但當上皇帝的唐太宗會督促史官,寫對他有利的「史實」。歷史只為勝者而寫。
惹起我連番聯想的是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的一篇文章,題為《歷史將在香港的一邊》,肥佬黎講起賣壹週刊之事,我對文章的第一、二句,深感同意。黎智英劈頭就說,「賣仔莫摸頭,賣《壹週刊》是不可逆轉的宿命。」但對文章最後的兩句,則不敢苟同。他說「歷史將在我們一邊,歷史將在香港的一邊。」
搞一個傳媒,成功就是成功,失敗就是失敗。經營失敗之後,被逼賣盤。賣仔莫摸頭,不要依依不捨,這是一個無可奈何但理性現實的決定。但把商業行為美化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徑,還把自己捆綁成歷史的代表,就有點兒陳義過高了。套用武俠小說家古龍經常的造句方式:是那種人一定不可以寫歷史的呢?不是文盲,而是死人。一份雜誌結了業或者賣走了,便不能再寫歷史,往後成敗已與自己無關,無法再創高峰,再展輝煌了。
關於《壹週刊》的敗亡,大家有不同的解釋。肥佬黎在文章的解釋是「《壹週刊》面對的衝擊更不止於瞬息萬變、翻天覆地的資訊科技革命。我敢誇口,環顧全球,沒有同業遇上過我們在採訪及廣告面對的杯葛制裁。」到底《壹週刊》的死因為何,可以逐一分析。
第一,杯葛制裁。這是一般人對《壹週刊》廣告劇減的解釋。親中派不在壹週刊落廣告是事實,但用這個理由去解釋《壹週刊》的失敗原因卻有點懶惰。我最近與一位前壹傳媒高層聊天,他亦提到這個原因。我反問他,如果香港的《壹週刊》和《蘋果日報》受到親中央的廣告商抵制,台灣應該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台灣的《蘋果日報》及《壹週刊》與香港一樣,這樣少廣告呢?那位高層為之語塞。
我們做科學實驗,都會有一個控制組(control group)。台灣的《壹週刊》就像控制組一樣,不受香港因素影響,但其命運卻與香港基本相同,至2017年3月底年度香港《壹週刊》廣告有5780萬元,比對上一年大跌46%,而同期台灣《壹週刊》廣告更差,只有4280萬元,比對上一年劇跌53%,不受抵制的台灣壹仔廣告跌得更多。當誇大了抵制的影響,就會忽略了問題的本質。
第二,數碼衝擊。數碼衝擊的確會有影響,不過,影響有多大呢?我有一個親身經驗,三年多前,《巴士的報》創刊的時候,《壹週刊》記者約我訪問,做一個當時新冒起的三大網媒的比較故事。記者約我在中大崇基學院做訪問。除了記者之外,還見到一名影相的攝影師和拍片的攝影師,據說會把訪問內容放上網。我很好奇地問記者,你們把採訪故事全放上網,還有人會花20元買雜誌嗎?記者答不到這個問題。我當時心想,他們為我如此濕碎的人物做訪問,出動到三個人,更把如此碎料也全數上網。如此採訪恐怕成本過高,效益會過低。由此可見,壹傳媒面對的所謂數碼衝擊,其實是自己製造出來的難題。

第三,策略錯誤。《壹週刊》總編輯黃麗裳表示,《壹週刊》的轉型數碼化的策略可能有問題。她說,「現時回想,只能形容是不務正業,同行有無輸得咁慘呢?我哋過去投資好多令hit rate好啲,推數碼化,但響雜誌未必適合。」其實不單止《壹週刊》,整個壹傳媒,把很多平面傳媒體內容全部免費放上網。這樣做,就令到平面媒體的銷路跌得比同業快,但網絡廣告收入增長填不了平面媒體廣告驚人下跌的黑洞。看三年前的平面媒體廣告,還有15億,現在只剩5.6億,只剩三分之一。然而,網絡廣告在三年前已達到6.4億元,目前仍是6.5億,即是說,平面廣告過去在三年內急跌,而數碼廣告在三年前已經見頂。試問,這樣向數碼轉移的策略,是否正確呢?不見了的9.4億平面廣告用什麼去填? 媒體集團犧牲平面媒體去全面做網,就會得出災難性的結果。
傳媒行業永遠會面臨各種類型的政治和環境變化的衝擊,最終還是要看經營者的營運能力,才能走過環境變化的窄門,成為死人堆裏的倖存者。就算不做勝者,也要做生還者,因為歷史不是為敗亡者而寫。
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