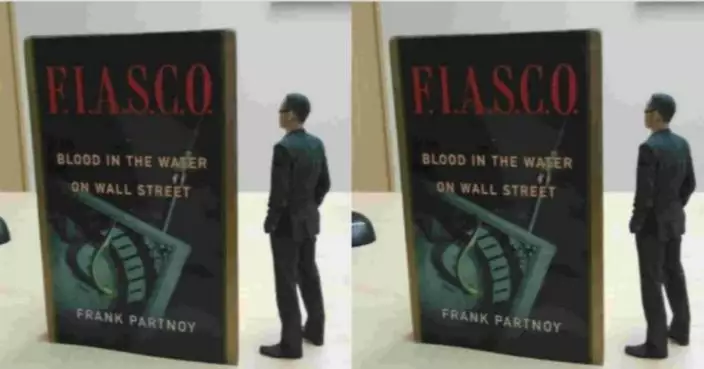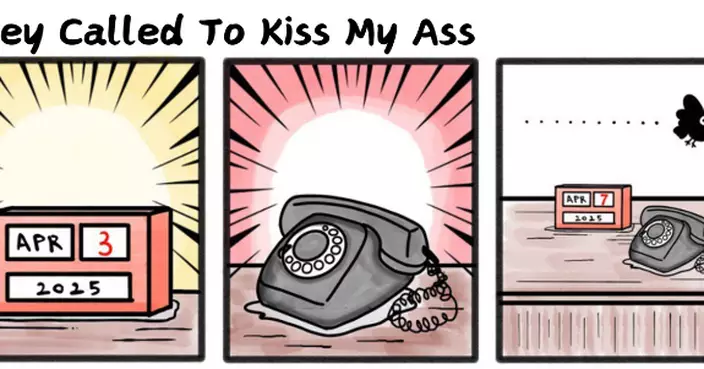作者: 李法言
香港是一個享有高度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的城市,按《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而香港在回歸後,所有市民都一直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言論自由並非代表可以不受限制及約束。濫用自由發表言論,還是有機會觸犯刑事或民事法律。
正如香港高等法院早前審理一宗涉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案件編號HCMA 457/23)。上訴人蘇浚鋒以呈請形式上訴,遭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高院暫委法官姚勳智認為,原審裁決沒有違反侵犯表達自由及平等的權利。
案件是發生在2021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前中大學生會會長蘇浚鋒涉在facebook轉載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呼籲投白票的帖文,蘇浚鋒承認「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罪,判監兩個月、緩刑18個月。蘇浚鋒其後以案件呈請方式提出上訴,法官在判詞中指出煽動市民不投票顯然不利於選舉過程,並浪費公共資源,本案施加言論自由的限制沒有超出所需,並且作出合理平衡。
從上述案件中可以看得出言論自由的權利,並非完全不受限制,而且言論自由一旦超越紅線,除了可能觸犯刑罪行外,也可能觸犯民事的「誹謗(defamation)」。根據香港法例第21章《誹謗條例》任何人或機構透過書面文字或說話,發布惡意言論去損害另一人的聲譽;或發布虛假消息,以求惡意中傷或誣衊他人,即屬誹謗。
概括而言,誹謗分為兩類:一類是永久形式誹謗 (Libel),即以書寫或其他永久性方式發佈;而另一類是短暫形式誹謗 (Slander),即以口述或其他短暫性方式發佈。
若要以民事程序控告他人誹謗,原告人要證明相關言論與事實不符,對方是惡意中傷。
但被告人抗辯首先可證明有關言論符合事實。另外亦可就言論不涉及或沒有針對原告或言論是有理據(justification) 、公允評論(fair comment)及是否受特權保護(qualified privilege)作為抗辯護理由。
以「公允評論」(fair comment)作為誹謗案抗辯理由會最經典案例,莫如律師謝偉俊1996年指「名嘴」鄭經翰及林旭華在電台節目中誹謗他,從而向鄭及林提出控告。謝偉俊在原審及上訴時皆獲判勝訴,獲賠償8萬元及贏得堂費,但案件在2001年上訴至終審庭時,出現峰迴路轉,終審法院裁定鄭一方上訴得直,終院亦在這案中,確立公允評論(fair comment)的原則,即被告一方在發表言論時,是真誠地相信其發表的是公允評論,即使其懷有偏見或別有用心,亦可以用作免責辯護,從而保障大眾就公眾利益發表意見時,可以用作抗辯理據。
但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當中,有些人喜歡為朋友改花名,例如叫一名熟朋友做 「排骨」,是否須因此而要負上誹謗的法律責任呢?任何可能會令他人受到憎恨或鄙視的字句,都會構成誹謗。不過,正如《Gatley on Libel and Slander》一書中提及,要確定這些字句是否有誹謗性,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嘲笑其他人以達至某程度上的幽默,經常會在生活裡發生。如有關字句不能動搖一個人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便不能被用作展開誹謗訴訟的理據。
不過,在一宗英國案例內 (Berkoff v Burchill & Anor.),Berkoff是著名的演員、導演兼作家,在一篇文章中,他被形容為「惡名昭彰、看來很可怕的人」。其後,作者在另一篇講述電影《怪物》的文章中,又將其中一個角色形容為與 Berkoff 一樣,指「『那隻怪物』與『Berkoff』 很相似,只是僅僅好看一點」。
Berkoff 指這些陳述令其他人把他理解成「可怕而醜陋」的人,因而具誹謗性。被告人申請將訴訟撤銷,原因是這些陳述,可能只會令人在情感上受到傷害或覺得憤怒,但並不算是誹謗。不過,法庭認為以這樣的描述去形容一個以演藝維生的人,令Berkoff在一般公眾心目中聲譽受損,足以構成誹謗罪。
由此可見,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界線,一個人不負責任地發言,對社會造成傷害(如叫人投白票),或損害他人名譽(話他人似怪物),都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法律ABC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