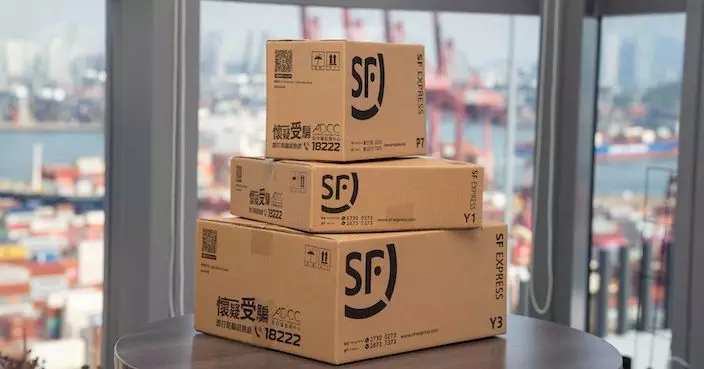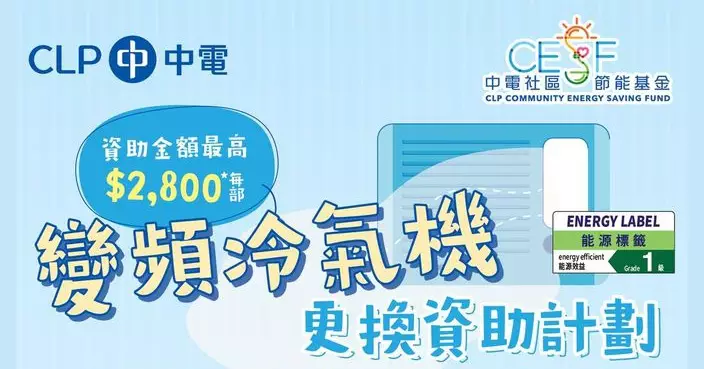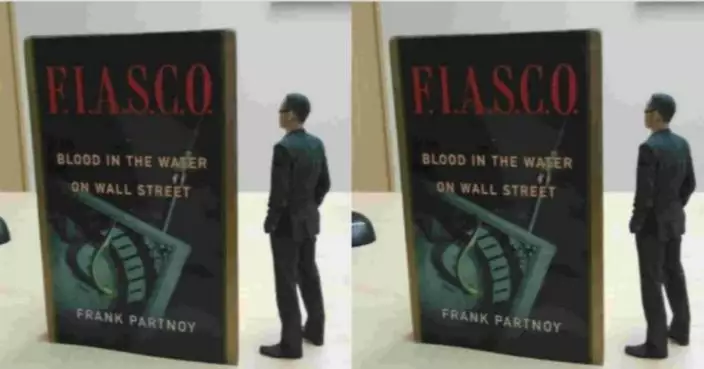作者: 李法言
香港的法律體系是普通法體系(Common law),與之相對的是大陸法體系(Continental law)。普通法源自英國,曾受英國管治的地區,多數都保留了普通法制度。
普通法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除了立法機構訂立的成文法(Statute)外,法庭判案的案例亦形成判例法(Case law),構成重要的法律內容,下級法院以後判案需要跟從。而在大陸法系,案例根本沒有約束力,法庭可以不跟從。
在普通法系的一些法律範疇,例如合約法、侵權法、財產法、行政法、部份刑事法、信託法等,基本概念和原則框架,都是來自判例,而並非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例。在普通法下,每一宗判案的理據所蘊含的法理原則,都可能具有法律的效力,這些判決構成判例(Precedent)。一般而言,上級法院判例,對下級法院是有約束力的。普通法的其他特點,包括以制衡行政權力為宗旨,傾向保障個人權利,以及採用對訟式的審訊程序等。
雖然說普通法系判例法很重要,但判例始終有限。香港各級法官只有約160名,另外還有約40名由執業律師或大律師擔任的兼任法官,每年即使審理大量個案,但這些個案都未必涉及重要的法律原則論述,形成判例法。即使《基本法》第8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可以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院判例,但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仍是重要的法律來源。
以2022至2024年3年計,平均每年在憲報刊登的法例(包括條例即Ordinance及附屬法例即Subsidiary legislation),都有200多項,過去3年在憲報刊登的法例總頁數,分別是6764頁、9886頁和7928頁。由此可見,雖然說香港是一個普通法體系,但立法機關制定的法例,才是主要的法律內容。當然,立法機關制定越來越多的法律,不等於法官的角色不重要,事實上在執行法律的時候,不時會產生詮釋理解問題,都可能成為訴訟爭議內容,法官對成文法例條文的詮釋,亦構成判例的一部份,成為成文法的延伸,不斷地為普通法體系增添新元素。
普通法制度下法官的角色,經常被人誤解,指「法官大晒」,事實上在有成文法涵蓋的範疇,法官不能任意判決,只能跟成文法律判案。法官的權限,只是對法例條文作權威解釋,而不是一槌定音地決定法律內容。立法機關如果認為法院的解釋不符合立法原意,曲解了法律,完全有權修改法例,進一步釐清立法原意。換言之,法律的解釋,最後以立法機關為依歸,不會出現法庭大抑或立法機關大的問題,在普通法制度裏,以立法機關為大,立法機關至上(Supremacy of legislature)的原則是牢不可破的,在普通法制度裏,立法機關享有最高的憲政地位。所以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扭轉法院對法例的解釋,不能視為輸打嬴要,反而是澄清了法庭對成文法的曲解。
而立法機關一般在釐清立法原意下立法,不會有回溯性,只對未來的判決有影響,不能夠逆轉之前判決中的勝負,對案中訴訟人沒有影響。但新立法可阻止法庭的錯誤解讀形成判例法,對未來的官司有影響。
按香港的一國兩制安排,《基本法》規定了《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制度」,這是其他普通法地區所沒有的。背後的理念,是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她制訂《基本法》,理所當然有權對它所訂立《基本法》的內容,作出最權威的解讀。人大常委會亦授權香港法院可以對《基本法》進行司法解釋。這個獨特的程序,是照顧香港的特殊的憲制安排,可以視為香港普通法的一大特色。
法律ABC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