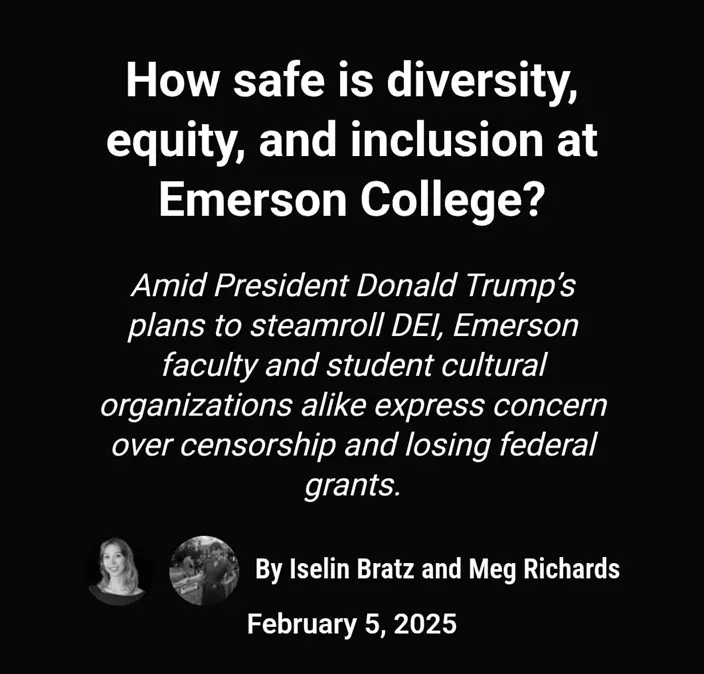96歲的英女王駕崩,她的一生,見證了大英帝國散射的餘暉,她本人就是一部活歷史書。
1952年,年僅26處的伊利沙伯二世即位。她的就職典禮首次以電視直播,她的加冕禮服,仍然代表著大英帝國無遠弗屆的領土。按她的指示,加冕禮服繡上英格蘭的都鐸薔薇、蘇格蘭的薊、威爾斯的韭蔥、愛爾蘭的三葉草、澳洲的金合歡、加拿大的楓葉、新西蘭的銀葉蕨、南非的海神花、印度和錫蘭的蓮、以及巴基斯坦的小麥、棉花等各地代表性的植物,顯示帝國橫跨歐、亞、非洲。不過,二戰令英國負債累累,這個「日不沒國」,正走向衰落。
英女王任內歷經15個首相,她任上的第一個首相,就是威名鼎盛的邱吉爾。邱吉爾領導英國在二次大戰慘勝。英國雖然打贏了仗,但陷入了饑餓和貧困當中。就在1945年,英國保守黨在大選中落敗,邱吉爾成為反對黨領袖。1951年邱吉爾再度當選首相,次年就遇上新登位的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一個78歲的老政客遇上一個26歲的年青女王,這一幕,在Netflix的《王冠》劇集中重現,現在看起來仍然別有味道。當年的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已經表露出強悍的作風,對邱吉爾亦非言聽計從。
二戰之後,英國國力衰敗,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英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英女王幫助組織英聯邦,想維持英國與獨立後殖民地的特殊關係,但亞、 非、拉的前殖民地國家,多數不賣賬。英女王多次出訪,去拉攏這些國家的關係,最兇險的一次,可算是1961年去非洲西部國家加納訪問。加納當時已經獨立,總統恩克魯瑪取代了英女王,成為加納的國家元首。英女王出訪之前,已盛傳恩克魯瑪可能會被行刺。當時英國的首相是麥美倫忠告英女王不要出訪該國,但是,英女王為了維持與殖民地的關係,堅持出訪加納,還與恩克魯瑪共舞。英女王深明作為國家元首的作用,希望透過親和的訪問,可以維繫已十分脆弱的前殖民地關係。麥美倫後來回憶說,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十分堅決,而且敬業樂業。
但大英帝國的沒落,並非可因個人的意願而轉移。只有少部份白人為主的前殖民地,願意和英國保持特殊關係,例如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不過到了70年代,英國進一步衰落,加拿大和澳洲都出現反對英國領導的舉措。加拿大於1982年通過將憲法的修改權,由英國議會轉移到加拿大議會,英國和加拿大的特殊憲政關係正式終結。澳洲則在1986年收回終審權,至此,英國樞密院不再對澳洲行使司法終審權,這個權力交回澳洲的高等法院。澳洲和英國的特殊關係,亦告終結。
當然,更大的事件是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這顆英聯邦內的最後明珠,終於脫落。
伊利沙伯二世終其一生,運用其超凡的堅忍和高強的能力,勉強維繫著這個搖搖欲墜的英聯邦。她駕崩之後,兒子查理斯接任王位,也將代表著英國王朝徹底沒落。今年4月,加拿大的民調顯示,55%的受訪者表示,只要英女王還活著,會支持君主立憲制,由英王作加拿大君主,但到查理斯國王執政後,支持率跌到34%。今年6月,澳洲的共和國事務助理部長齊索斯威特說,雖然英女王一直以來是「夢幻般的君主」,但澳洲已經足夠成熟,任命自己的國家元首,來取代查理斯陛下。
伊利沙伯二世的一生,見證著大英帝國由盛轉衰的歷史。而歷史有如滾滾洪流,不會因個人的意願而轉移。
盧永雄
想不到一個國家可以流氓到這種程度,對外是一副面孔,對內又是完全相反的一副面孔。
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6名內地及及香港的官員,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指制裁是「因為那些人剝奪了香港人的自由,同時對美國領土上的活躍分子實施跨境壓逼。」
流亡美國的黑暴份子如許穎婷等人,一直遊說魯比奧等人對香港官員實施制裁。魯比奧早已把制裁名單握在手上,但到今天才突然發出制裁,恐怕與長和暫緩出售巴拿馬等港口的交易有關。美國這次的制裁是隔空敲打長和,逼他們盡快簽約,所以誰還傻得說這是「純商業交易」,就真是天真得可以了。
由特朗普政府的官員,說要捍衛自由和反對跨境壓逼,那種黑色幽默的意味,真是濃得化不開了。
第一,卡壓自由。美國的《國安法》不但比香港強硬得多,而特朗普政府超越法律對各種自由的卡壓手段,的確令人大開眼界,其中一招就是直接削減撥款。特朗普可以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暫停對衛生科研和大學的撥款,並在3月15日停止對《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的撥款,目的是整治這些機構裡支持民主黨的人員,徹底打碎他們的飯碗,而矛頭焦點就是針對所謂「DEI」政策(多元、平等和包容政策),直指這些政策要求機構聘用跨性別人士,這些人就是特朗普的反對者。
在特朗普斷水喉之後,那些機構紛紛跪低,其中一個就是哥倫比亞大學,完全接納了特朗普對大學學術自由的干預。特朗普政府大力壓制美國人的自由,為何還可以妄稱要保護香港人的自由呢?
第二,跨境壓逼。說到跨國干預,香港通緝幾個流亡到美國的黑暴份子,真是小兒科之極了。美國的跨國干預是針對整個國家或地區,特朗普要將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個州,要取回巴拿馬運河,還要強奪丹麥屬下的格陵蘭,到最近還聲稱為奪取格陵蘭會不惜動武。而據格陵蘭傳媒做的民調顯示,85%的格陵蘭居民不想成為美國人。特朗普威脅用武力去強奪他國的領土,這些才真正是魯比奧口中的跨國壓逼(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美國就是拿著她的雙重標準,借許穎婷這些人遞來的刀,制裁內地和香港的官員,壓逼中國就範,恐嚇長和要把巴拿馬的碼頭賣給美國公司。
在黑色幽默的背後,真正悲哀是許穎婷這種流亡的港人。她在2014年加入學民思潮,之後在香港大搞本土派運動,後來去了美國麻省波士頓愛默生學院讀新聞系,在2020年10月宣布流亡美國,在2024年4月宣布成功獲得美國政治庇護,成為首名獲得美國政府批出政治庇護的香港人,拿到美國的綠卡。她之後在美國到處搞政治遊說,要求美國政府制裁香港官員。不過她乞求的對象,剛好就是大力扼殺美國民主和自由的特朗普政府官員和共和黨議員。
許穎婷在香港十分激進,但去到美國就變成乖乖女,她顯然不喜歡特朗普,但又不敢開罵。在特朗普2020年競選連任時,她未申請到政治庇護,已經非常低調,在facebook評論美國選舉時不敢批評特朗普。到2024年特朗普再次參選,許穎婷更噤若寒蟬,不再評論美國的選舉事。直到最近,特朗普政府要關閉《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就踩到許穎婷最痛之處。她在facebook直言「《自由亞洲電台》可以說是對我有恩。自2021年起,我以不同的方式與《自由亞洲電台》合作,也正是因為這個機會,我才能搬到華府,在美國政治核心打滾。」
但許穎婷對特朗普停止資助《自由亞洲電台》的評論,仍然溫和得可以,不敢罵特朗普半句,只是說「美國政府削資的決定是否合理,仍然值得深思」。
許穎婷面對特朗普政府這樣橫蠻無理地削資關停於她有恩的媒體,只作一句「值得深思」的評論,如果許穎婷當日在香港都是這麼溫和的話,就根本不需要流亡了。

2023年12月,許穎婷(中)和另一流亡份子邵嵐(左)和美國共和黨參議員丹.蘇利文(右)見面,遊說蘇利文支持制裁香港官員。如今丹.蘇利文是一個剷除DEI政策的活躍份子,力主在他所屬的阿肯色州立法去除所有大學的DEI相關課程。
許穎婷的確是害怕特朗普政府,因為特朗普政府會毫不猶疑地將類似她那樣的人驅逐出境。3月8日,美國移民部門拘捕哥倫比亞大學一個巴勒斯坦裔的研究生哈利勒,因為他曾經參加過反對以色列出兵加沙的抗議活動。哈利勒已經擁有美國綠卡,他的妻子是美國公民,但仍要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厄運。美國國土安全部在3月28日再宣布,拘捕另一名哥大學生鄭允瑞。鄭允瑞是韓裔,自小跟隨父母移民美國,也擁有美國綠卡,因為參與哥大校園的反猶抗議活動被捕,目前也面臨被驅逐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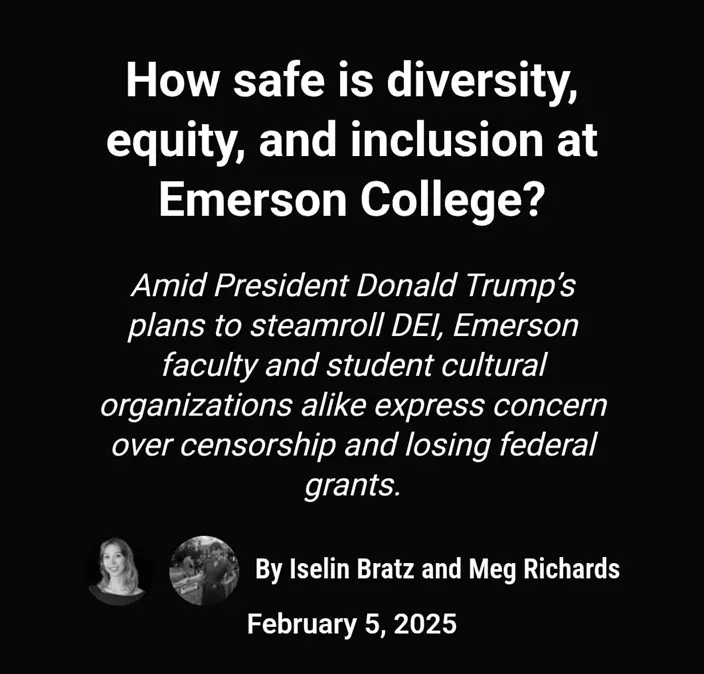
愛默生書院成員的哀嗚
許穎婷的母校愛默生書院亦正發出哀鳴,2月5日有書院成員在愛默生書院學生報發表文章,題為《多元平等包容 在愛默生書院有多安全》,內文直指總統特朗普意圖取消DEI政策,愛默生書院的師生及文化組織面臨重大壓力,不單怕會被學術審查,更怕會失去聯邦撥款,他們形容這是「情緒恐怖主義」、「學術審查」、「超級民族主義」,這就如60年代末的情況一樣。相信許穎婷都知道母校人員的哀歌,但是她不敢吭一聲,不敢出來示威抗議特朗普政府,不敢鼓勵人上街扔汽油彈去反對美國政府要取消「DEI」政策,她怕特朗普政府會驅逐她出境。特區政府已經吊銷了許穎婷的護照,如果她被美國驅逐出境,恐怕會成為國際人球。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許穎婷們這些向美國遞刀,最後會淪為對方用完即棄的棋子,下場悲慘。而被美國制裁的官員們,就是國家的英雄。誰登上了美國的制裁榜,就是上了我國的光榮榜,前路光明。
盧永雄